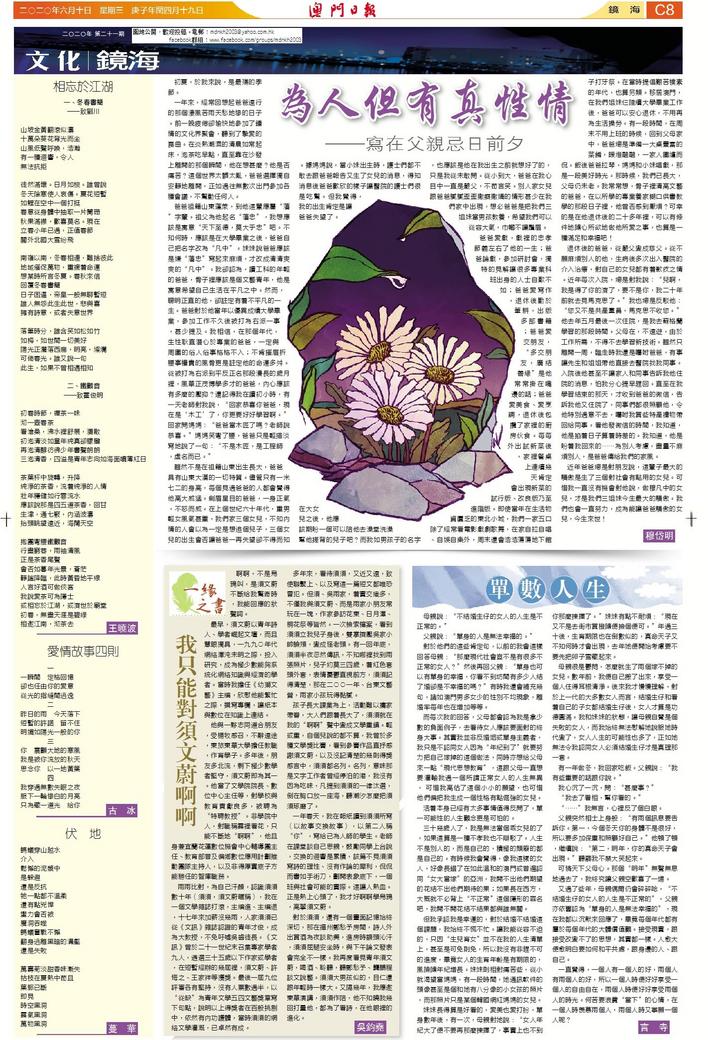我只能對須文蔚啊啊
啊啊,不是烏鴉叫,是須文蔚不斷給我驚奇時,我能回應的狀聲詞。
最早,須文蔚以青年詩人、學者崛起文壇,而且慧眼獨具,一九九○年代網絡渾沌未明之際,投入研究,成為極少數能夠系統化網絡知識與經濟的學者。當時我擔任《幼獅文藝》主編,欣慰他能繁忙之際,撰寫專欄,讓紙本與數位在知識上連結。
他與一夥志同道合朋友,受楊牧感召,不辭遠途,東旅東華大學擔任教職,作育學子。多年後,朋友多北流,剩下極少數學者堅守,須文蔚即為其一。他當了文學院院長、數位中心主任等,對學校與教育貢獻良多,被聘為“特聘教授”。非學院中人,對職稱霧裡看花,只能不斷地“啊啊”,他且身兼宜蘭花蓮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主任、教育部普及偏鄉數位應用計劃推動團隊主持人,以及非得厚實底子方能勝任的智庫職務。
兩兩比對,為自己汗顏,認識須須數十年(須須,須文蔚暱稱),我在一個文學雜誌打滾,主編進、主編退,十七年來加薪沒幾兩,人家須須已從《文訊》雜誌認證的青年才俊,成為大教授,不免吁噓吳齒徒長。《文訊》曾於二十一世紀末召集專家學者九人,遴選三十五歲以下作家或學者,在短暫經辦的幾屆裡,須文蔚、許悔之、王家祥等獲獎。最後一屆九位評審各有堅持,沒有人票數過半,以“從缺”為青年文學五四文藝獎章寫下句點,說明以上得獎者在百般挑剔中,依然有內功護體,當時須須的網絡文學灌溉,已卓然有成。
多年來,看待須須,又近又遠,致使聯繫上、以及寫這一篇短文都唯恐冒犯。但須、吳兩家,着實交織多,不僅我與須文蔚、而是兩家小朋友常玩在一塊,作家參訪花東、日月潭、桐花祭等皆然。一次檢索檔案,看到須須立我兒子身後,雙掌擠壓吳家小帥臉頰,變成怪老頭。有一回年底,須須半夜忽然傳訊,不知哪裡找到兩張照片,兒子約莫三四歲,着紅色套頭外套,表情憂鬱直視前方,須須記得清楚,那在二○○一年、台東文藝營,兩家小孩玩得黏膩。
孩子長大課業為上,活動難以攜家帶眷,大人們跟着長大了,須須就在我的“啊啊”聲中變成文學重鎮。輕或重,自個兒說的都不算,我曾於多種文學獎比賽,看到參賽作品直抒感謝須文蔚,以及沒記清楚的幾則得獎感言中,須須都名列。名列,意味那是文字工作者曾經停泊的港,我沒有因為吃味,凡提到須須的一律汰選,倒在胸口放一座海,聽潮汐怎麼把須須琢磨了。
一年春天,我在報紙讀到須須所寫〈以故事交換故事〉,以第二人稱“你”,寫給已為人師的學生。老師在課堂談自己思親,鼓勵同學上台說,交換的迴響是累積,該篇不見須須寫詩的理性、沒有作論的犀利,侃侃而書如手術刀,劃開表象底下,一個班與社會可能的實際。這讓人熱血。正是熱上心頭了,我才好啊啊學烏鴉,高攀須文蔚。
對於須須,還有一個畫面記憶始終深切,那在福州鄭愁予房間,詩人外出買酒為夜談助興,進房時額頭沁汗,須須屈腿安坐時,與下午論文發表會完全不一樣。我再度看見青年須文蔚,喝酒、聆聽,聽鄭愁予、龔鵬程談文說藝。須須大男孩似的,目仁還跟年輕時一樣大。又隔幾年,我應邀東華演講,須須作陪,他不知曉我幾回打量他,都為了看詩,在他眼裡的進化。
吳鈞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