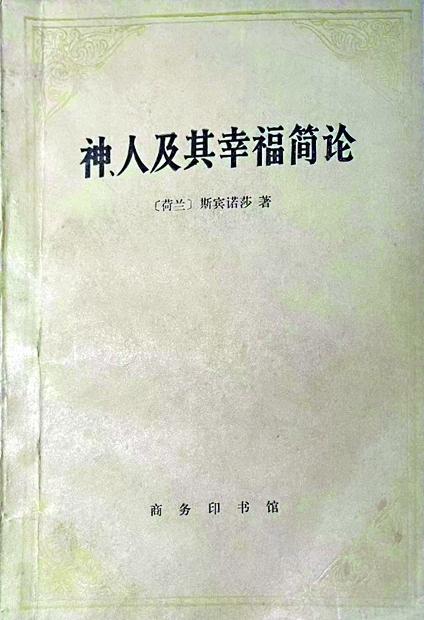“被迫害者轉而成了迫害者”不能重演
或許是學哲學專業的緣故,荷蘭藉猶太人迪克特 ·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是自己較為喜歡的一位古典哲學家,因此,他的《神、人及其幸福簡論》(下簡稱《簡論》)也曾斷斷續續讀過好幾遍,巴以衝突發生後,再度翻開了它。
據我所知,歷史上,西班牙早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就是猶太人的棲息之所,當時,猶太人也曾享有相當的權力,生活也十分順遂。而到了一四九二年,擺在猶太人面前的困境是:如不接受浸禮(改變宗教信仰),就要被驅逐出境,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於是,那些寧要流浪而不願意接受浸禮的猶太人出境流浪時,便嚴禁帶走他們所創造的財富,特別是黃金和銀幣。到頭來,有二十萬因忠於宗教信仰的猶太人寧願放棄財富,被迫離開故鄉,開始流浪,他們之中有數以千計的人由於經受不住顛沛流離的折磨而夭折。當時,儘管約有五萬人以韜光養晦之計,選擇了浸禮,並留在了西班牙,然而在他們的心底仍然堅持自己是猶太人。
一四九二年,托克馬達(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迫使國王下令懲治不改宗的猶太人,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卑鄙之徒則到處尋找新教徒中的猶太親族的線索,用最微不足道的口實來作為充分的證據,迫害更加殘忍。一直以來,猶太人以自己的猶太教教義在那裡爭取着、掙扎着,他們承諾願意用可觀的財產為促進阿姆斯特丹貿易繁榮貢獻力量,同時又證明他們是在迫害之下逃亡出來的,這才允許居住下來。儘管猶太人有着自己民族的朝聖節,還有慶祝以色列人曾經得救的節日,如普林節,即便如此,一六五七年時,他們依然沒有被承認是公民。
在這種境遇下生活着,猶太教教會的當權者,從“被迫害者轉而成了迫害者”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特別是當他們的命運有所改善,而聯合的需要已經不再成為燃眉之急時,這種不容異己的矛盾變得愈來愈突出了。比如,有一位叫柯斯泰的人想重回猶太教,當時,猶太教公會也公開撤銷了他的罪惡主張,但處罰是必須的:一是接受三十九鞭笞,二是趴在猶太教公會的門檻上,讓離開會堂的教徒從他的身上跨越過去。柯斯泰的確一一照着做到了,然而他遭受的精神上的恥辱始終揮之不去,於是不久就自殺。
斯賓諾莎更是典型,他不光被革除出猶太教,同時還被從以色列人中剪除出去。一六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阿姆斯特丹猶太教公會宣判把斯賓諾莎革出教門,並從以色列人中剪除。書中四十二頁說道:“並按摩西律法所有詛咒咒詛他”,“任何人都不得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與他交往,不得對他表示任何好感,不得與他同住一屋,不得與他同在二米的距離之內,不得讀他的著述和書寫的任何東西。”
在《簡論》中,有一個很長的章節在闡述“被壓迫者轉而成為壓迫者”。早前讀它,多數匆匆一瞥,不以為意;這次讀它,仿若被牽住耳朵聆聽一番。歷史上,猶太民族多災多難,他們有過多次的被壓迫、被剝奪、被驅逐,生活從未安穩過。尤為慘烈的是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那段時間,有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殺害,為了銘記那段歷史,猶太人還制定了“大屠殺紀念日”。雖說快過去一個世紀了,再去看那段歷史的電影、文字和圖片,依然催人落淚。
現在的以色列,由曾經的被壓迫者轉變成現今的壓迫者,卻感到無可奈何。巴以衝突,以色列大有一種你巴勒斯坦不服,我要打得你服的態勢。他說要消滅哈馬斯,而哈馬斯消滅得了嗎?回顧過去,包括納粹以前的那些人,誰不曾想把猶太人整個種族消滅掉?然而在最不利的情況下,以猶太人採用了韜光養晦之計,表面上歸順,而骨子裡在不斷地積蓄力量,一有機會就反抗、就獨立。當年的以色列,當年的猶太人能從那種最不利的生存方式,最殘酷的情況下堅持下來,並且走了出來,難道人家哈馬斯,人家巴勒斯坦就不能效仿嗎?千萬記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硬道理。
巴以衝突,帶來的是民不聊生流離失所,帶來的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戰火中的家園成了人間地獄,那不是以色列人,更不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在目前的形勢下,還是請佔據主導地位的以色列人,記一下你們的前輩斯賓諾莎講的那句話:“我享受着人生的幸福,而且要勉力去生活得幸福,不是去過那種悲哀和嗟歎的生活,而是過平靜、快樂、令人高興的生活。”本人相信,以色列人還是熱愛那種平靜、快樂、令人高興的生活的。
有道是婚姻勸成,是非勸散,巴以衝突,坐下來談才是出路。
昌 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