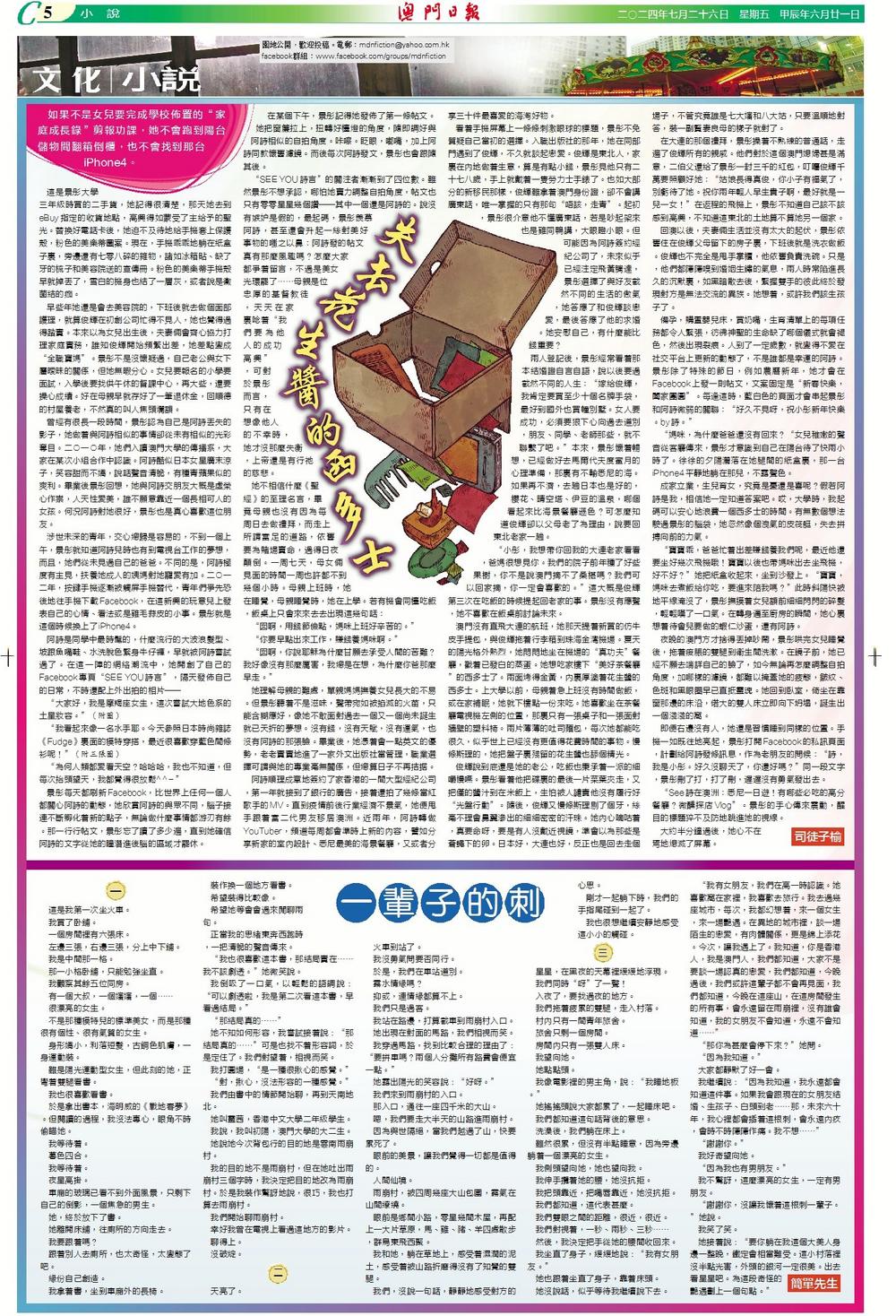失去花生醬的西多士
如果不是女兒要完成學校佈置的“家庭成長錄”剪報功課,她不會跑到陽台儲物間翻箱倒櫃,也不會找到那台iPhone4。
這是景彤大學三年級時買的二手貨,她記得很清楚,那天她去到eBuy指定的收貨地點,高興得如蒙受了主給予的聖光。替換好電話卡後,她迫不及待地給手機套上保護殼,粉色的美樂蒂圖案。現在,手機乖乖地躺在紙盒子裏,旁邊還有七零八碎的雜物,諸如冰箱貼、缺了牙的梳子和美容院送的宣傳冊。粉色的美樂蒂手機殼早就掉丟了,雪白的機身也結了一層灰,或者說是黴菌結的痂。
早些年她還是會去美容院的,下班後就去做個面部護理,就算俊輝在初創公司忙得不見人,她也覺得過得踏實。本來以為女兒出生後,夫妻倆會齊心協力打理家庭實務,誰知俊輝開始頻繁出差,她差點變成“全職寶媽”。景彤不是沒懷疑過,自己老公與女下屬曖昧的關係,但她無暇分心。女兒要報名的小學要面試,入學後要找供午休的督課中心,再大些,還要操心成績。好在母親早就存好了一筆退休金,回順德的村屋養老,不然真的叫人焦頭爛額。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景彤認為自己是阿詩丟失的影子,她做着與阿詩相似的事情卻從未有相似的光彩奪目。二○一○年,她們入讀澳門大學的傳播系,大家在某次小組合作中認識。阿詩酷似日本女星廣末涼子,笑容甜而不嬌,說話聲音清脆,有種青蘋果似的爽利。畢業後景彤回想,她與阿詩交朋友大概是虛榮心作祟,人天性愛美,誰不願意靠近一個長相可人的女孩。何況阿詩對她很好,景彤也是真心喜歡這位朋友。
涉世未深的青年,交心總歸是容易的,不到一個上午,景彤就知道阿詩兒時也有到電視台工作的夢想,而且,她們從未見過自己的爸爸。不同的是,阿詩極度有主見,扶養她成人的姨媽對她寵愛有加。二○一二年,按鍵手機逐漸被觸屏手機替代,青年們爭先恐後地往手機下載Facebook,在這新興的玩意兒上發表自己的心情、看法或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景彤就是這個時候換上了iPhone4。
阿詩是同學中最時髦的,什麼流行的大波浪髮型、坡跟魚嘴鞋、水洗脫色緊身牛仔褲,早就被阿詩嘗試過了。在這一陣的網絡潮流中,她開創了自己的Facebook專頁“SEE YOU詩言”,隔天發佈自己的日常,不時還配上外出拍的相片——
“大家好,我是摩羯座女生,這次嘗試大地色系的土星妝容。”(附圖)
“我看起來像一名水手耶。今天參照日本時尚雜誌《Fudge》裏面的模特穿搭,最近很喜歡穿藍色間條衫呢!”(附三張圖)
“為何人類都愛看天空?哈哈哈,我也不知道,但每次抬頭望天,我都覺得很放鬆^ ^~”
景彤每天都刷新Facebook,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關心阿詩的動態,她欣賞阿詩的與眾不同,腦子接連不斷孵化着新的點子,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游刃有餘。那一行行帖文,景彤忘了讀了多少遍,直到她確信阿詩的文字從她的瞳潛進後腦的區域才罷休。
在某個下午,景彤記得她發佈了第一條帖文。她把窗簾拉上,扭轉好檯燈的角度,隨即調好與阿詩相似的自拍角度。咔嚓。眨眼,嘟嘴,加上阿詩同款懷舊濾鏡。而後每次阿詩發文,景彤也會跟隨其後。
“SEE YOU詩言”的關注者漸漸到了四位數。雖然景彤不想承認,哪怕她賣力調整自拍角度,帖文也只有零零星星幾個讚——其中一個還是阿詩的。說沒有嫉妒是假的,最起碼,景彤羨慕阿詩,甚至還會升起一絲對美好事物的嗤之以鼻:阿詩發的帖文真有那麼風趣嗎?怎麼大家都爭着留言,不過是美女光環罷了……母親是位忠厚的基督教徒,天天在家裏唸着“我們要為他人的成功高興”,可對於景彤而言,只有在想像他人的不幸時,她才沒那麼失衡,上帝還是有行祂的慈悲。
她不相信什麼《聖經》的至理名言,畢竟母親也沒有因為每周日去做禮拜,而走上所謂富足的道路,依舊要為賭場賣命,過得日夜顛倒。一周七天,母女倆見面的時間一周也許都不到幾個小時。母親上班時,她在睡覺,母親睡覺時,她在上學。若有機會同檯吃飯,飯桌上只會來來去去出現這幾句話:
“囡啊,用錢節儉點,媽咪上班好辛苦的。”
“你要早點出來工作,賺錢養媽咪啊。”
“囡啊,你說耶穌為什麼甘願去承受人間的苦難?我好像沒有那麼厲害,我總是在想,為什麼你爸那麼早走。”
她理解母親的難處,單親媽媽撫養女兒長大的不易。但景彤聽着不是滋味,聲帶宛如被掐滅的火苗,只能含糊應好,像她不敢面對過去一個又一個尚未誕生就已夭折的夢想。沒有錢,沒有天賦,沒有運氣,也沒有阿詩的那張臉。畢業後,她憑着會一點英文的優勢,老老實實地進了一家外文出版社當管理,職業選擇可謂與她的專業毫無關係,但總算日子不再拮据。
阿詩順理成章地簽約了家香港的一間大型經紀公司,第一年就接到了銀行的廣告,接着還拍了幾條當紅歌手的MV。直到疫情前後行業經濟不景氣,她便甩手跟着富二代男友移居澳洲。近兩年,阿詩轉做YouTuber,頻道每周都會準時上新的內容,譬如分享新家的室內設計、悉尼最美的海景餐廳,又或者分享三十件最喜愛的海淘好物。
看着手機屏幕上一條條刺激眼球的標題,景彤不免質疑自己當初的選擇。入職出版社的那年,她在同部門遇到了俊輝,不久就談起戀愛。俊輝是東北人,家裏在內地做着生意,算是有點小錢,景彤見他只有二十七八歲,手上就戴着一隻勞力士手錶了。也如大部分的新移民那樣,俊輝雖拿着澳門身份證,卻不會講廣東話,唯一掌握的只有那句“唔該,走青”。起初,景彤很介意他不懂廣東話,若是吵起架來也是雞同鴨講,大眼瞪小眼。但可能因為阿詩簽約經紀公司了,未來似乎已經注定飛黃騰達,景彤選擇了與好友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傲氣,她答應了和俊輝談戀愛,最後答應了他的求婚。她安慰自己,有什麼能比錢重要?
兩人登記後,景彤經常看着那本結婚證自言自語,說以後要過截然不同的人生:“嫁給俊輝,我肯定要買至少十個名牌手袋,最好到國外也買幢別墅。女人要成功,必須要狠下心向過去道別,朋友、同學、老師那些,就不聯繫了吧。”本來,景彤懷着暢想,已經做好去馬爾代夫度蜜月的心理準備,那裏有不輸悉尼的海。如果再不濟,去趟日本也是好的,櫻花、晴空塔、伊豆的溫泉,哪個看起來比海景餐廳遜色?可怎麼知道俊輝卻以父母老了為理由,說要回東北老家一趟。
“小彤,我想帶你回我的大連老家看看,爸媽很想見你。我們的院子前年種了好些果樹,你不是說澳門摘不了桑椹嗎?我們可以回家摘,你一定會喜歡的。”這大概是俊輝第三次在吃飯的時候提起回老家的事。景彤沒有應聲,她不喜歡在飯桌前討論未來。
澳門沒有直飛大連的航班,她那天提着新買的仿牛皮手提包,與俊輝拖着行李箱到珠海金灣機場。夏天的陽光格外熱烈,她悶悶地坐在機場的“真功夫”餐廳,戳着已發白的蒸蛋。她想吃家樓下“美好茶餐廳”的西多士了。兩面烤得金黃,內裏厚塗着花生醬的西多士。上大學以前,母親着急上班沒有時間做飯,或在家補眠,她就下樓點一份來吃。她喜歡坐在茶餐廳電視機左側的位置,那裏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張面對牆壁的塑料椅。兩片薄薄的吐司麵包,每次她都能吃很久,似乎世上已經沒有更值得花費時間的事物。慢條斯理的,她把盤子裏殘留的花生醬也舔個精光。
俊輝說到底還是她的老公,吃飯也秉承着一派的細嚼慢嚥。景彤看着他把碟裏的最後一片菜葉夾走,又把僅的醬汁到在米飯上,生怕被人譴責他沒有履行好“光盤行動”。隨後,俊輝又慢條斯理剔了個牙,絲毫不理會鼻翼滲出的細細密密的汗珠。她內心嘀咕着,真要命呀,要是有人沒戴近視鏡,準會以為那些是蒼蠅下的卵。日本好,大連也好,反正也是回去走個場子,不管究竟誰是七大嬸和八大姑,只要溫順地對答,裝一副賢妻良母的樣子就對了。
在大連的那個禮拜,景彤操着不熟練的普通話,走遍了俊輝所有的親戚。他們對於這個澳門媳婦甚是滿意,二伯父還給了景彤一封三千的紅包,叮囑俊輝千萬要照顧好她:“姑娘長得真俊,你小子有福氣了,別虧待了她。祝你兩年輕人早生貴子啊,最好就是一兒一女!”在返程的飛機上,景彤不知道自己該不該感到高興,不知道這東北的土地算不算她另一個家。
回澳以後,夫妻倆生活並沒有太大的起伏,景彤依舊住在俊輝父母留下的房子裏,下班後就是洗衣做飯。俊輝也不完全是甩手掌櫃,他依舊負責洗碗。只是,他們都隱隱嗅到婚姻生鏽的氣息,兩人時常陷進長久的沉默裏,如黑暗散去後,緊握雙手的彼此終於發現對方是無法交流的異族。她想着,或許我們該生孩子了。
備孕,購置嬰兒床,買奶嘴,生育清單上的每項任務都令人緊張,彷彿神聖的生命缺了哪個儀式就會褪色,然後出現裂痕。人到了一定歲數,就變得不愛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的動態了,不是誰都是幸運的阿詩。景彤除了特殊的節日,例如農曆新年,她才會在Facebook上發一則帖文,文案固定是“新春快樂,闔家團圓”。每逢這時,藍白色的頁面才會串起景彤和阿詩微弱的關聯:“好久不見呀,祝小彤新年快樂。by詩。”
“媽咪,為什麼爸爸還沒有回來?“女兒稚嫩的聲音從客廳傳來,景彤才意識到自己在陽台待了快兩小時了。徐徐的夕陽灑落在她腿間的紙盒裏,那一台iPhone4平靜地躺在那兒,不露聲色。
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究竟是憂還是喜呢?假若阿詩是我,相信她一定知道答案吧。哎,大學時,我起碼可以安心地浪費一個西多士的時間。有無數個想法駛過景彤的腦袋,她忽然像個洩氣的皮筏艇,失去拼搏向前的力氣。
“寶寶乖,爸爸忙着出差賺錢養我們呢,最近他還要坐好幾次飛機哦!寶寶以後也帶媽咪出去坐飛機,好不好?”她把紙盒收起來,坐到沙發上。“寶寶,媽咪去煮飯給你吃,要進來陪我嗎?”此時斜陽快被地平線淹沒了,景彤撫摸着女兒額前細細閃閃的碎髮,輕輕嘆了一口氣。在轉身邁至廚房的瞬間,她心裏想着待會兒要做的蝦仁炒蛋,還有阿詩。
夜晚的澳門方才捨得丟掉吵鬧,景彤哄完女兒睡覺後,拖着痠脹的雙腿到衛生間洗漱。在鏡子前,她已經不願去端詳自己的臉了,如今無論再怎麼調整自拍角度,加哪樣的濾鏡,都難以掩蓋她的疲態,皺紋、色斑和黑眼圈早已直抵靈魂。她回到臥室,倚坐在靠窗那邊的床沿,偌大的雙人床立即向下坍塌,誕生出一個淺淺的窩。
即便右邊沒有人,她還是習慣睡到同樣的位置。手機一如既往地亮起,景彤打開Facebook的私訊頁面,計劃給阿詩發條訊息,作為老朋友的問候:“詩,我是小彤。好久沒聊天了,你還好嗎?”同一段文字,景彤刪了打,打了刪,遲遲沒有勇氣發出去。
“See詩在澳洲:悉尼一日遊!有哪些必吃的高分餐廳?微醺探店Vlog”。景彤的手心傳來震動,醒目的標題猝不及防地跳進她的視線。
大約半分鐘過後,她心不在焉地熄滅了屏幕。
司徒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