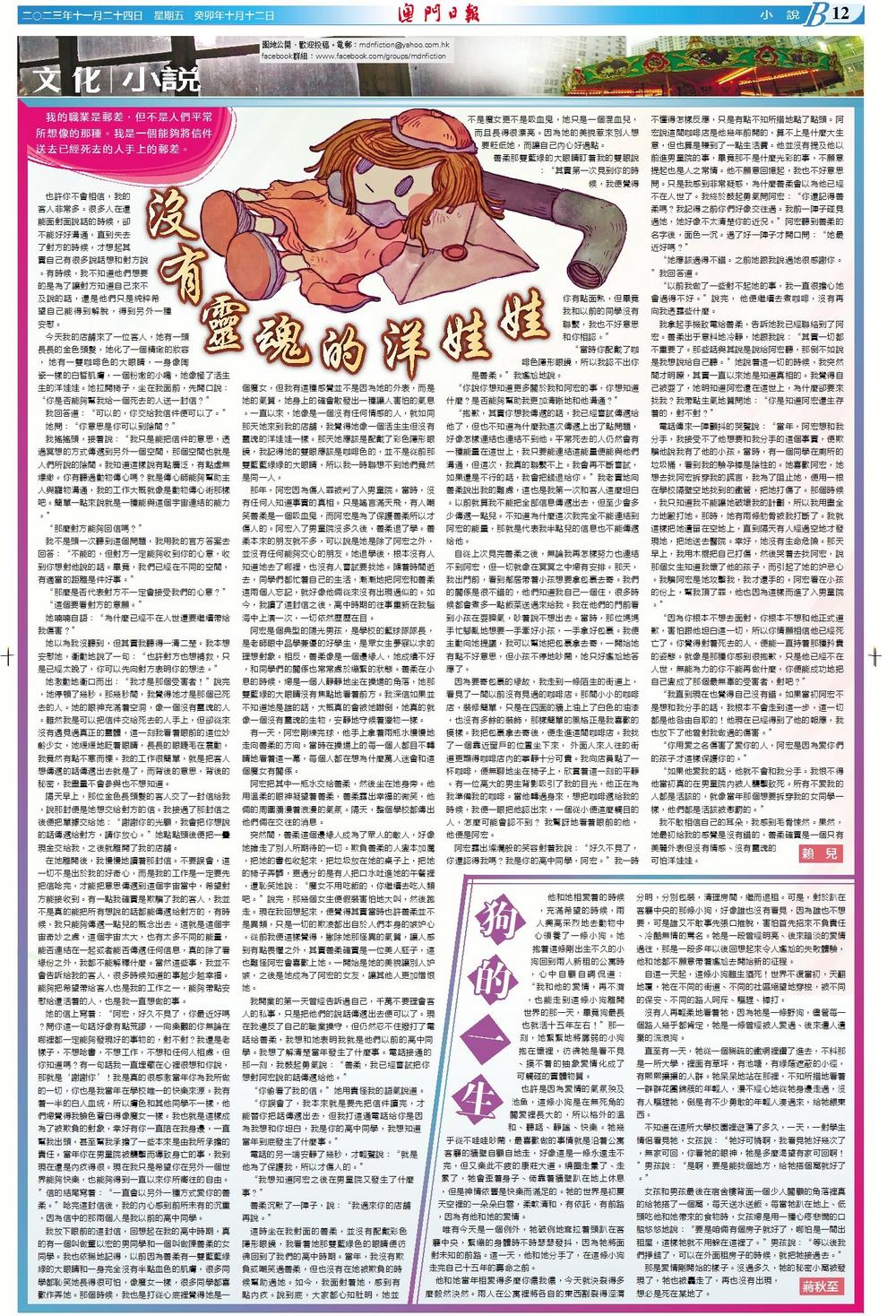沒有靈魂的洋娃娃
我的職業是郵差,但不是人們平常所想像的那種。我是一個能夠將信件送去已經死去的人手上的郵差。
也許你不會相信,我的客人非常多。很多人在還能面對面說話的時候,卻不能好好溝通,直到失去了對方的時候,才想起其實自己有很多說話想和對方說。有時候,我不知道他們想要的是為了讓對方知道自己來不及說的話,還是他們只是純粹希望自己能得到解脫,得到另外一種安慰。
今天我的店舖來了一位客人,她有一頭長長的金色頭髮,她化了一個精緻的妝容, 她有一雙咖啡色的大眼睛,一身像陶瓷一樣的白皙肌膚,一個粉嫩的小嘴,她像極了活生生的洋娃娃。她拉開椅子,坐在我面前,先開口說:“你是否能夠幫我給一個死去的人送一封信?”
我回答道:“可以的,你交給我信件便可以了。”
她問:“你意思是你可以到陰間?”
我搖搖頭,接着說:“我只是能把信件的意思,透過冥想的方式傳遞到另外一個空間,那個空間也就是人們所說的陰間。我知道這樣說有點廣泛,有點虛無縹緲。你有聽過動物傳心嗎?就是傳心師能夠幫助主人與寵物溝通,我的工作大概就像是動物傳心術那樣吧。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一種能與這個宇宙連結的能力。”
“那麼對方能夠回信嗎?”
我不是頭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我用我的官方答案去回答:“不能的,但對方一定能夠收到你的心意,收到你想對他說的話。畢竟,我們已經在不同的空間,有適當的距離是件好事。”
“那麼是否代表對方不一定會接受我們的心意?”
“這個要看對方的意願。”
她喃喃自語:“為什麼已經不在人世還要繼續帶給我傷害?”
她以為我沒聽到,但其實我聽得一清二楚。我本想安慰她,衝動地說了一句:“也許對方也想補救,只是已經太晚了,你可以先向對方表明你的想法。”
她激動地衝口而出:“我才是那個受害者!”說完,她停頓了幾秒。那幾秒間,我覺得她才是那個已死去的人。她的眼神充滿着空洞,像一個沒有靈魂的人。雖然我是可以把信件交給死去的人手上,但卻從來沒有遇見過真正的靈體,這一刻我看着眼前的這位妙齡少女,她緩緩地眨着眼睛,長長的眼睫毛在震動,我竟然有點不寒而慄。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把客人想傳遞的話傳遞出去就是了,而背後的意思,背後的秘密,我盡量不會參與也不想知道。
隔天早上,那位金色長頭髮的客人交了一封信給我,說那封便是她想交給對方的信。我接過了那封信之後便把單據交給她:“謝謝你的光顧,我會把你想說的話傳遞給對方,請你放心。”她點點頭後便把一疊現金交給我,之後就離開了我的店舖。
在她離開後,我慢慢地讀着那封信。不要誤會,這一切不是出於我的好奇心,而是我的工作是一定要先把信唸完,才能把意思傳遞到這個宇宙當中,希望對方能接收到。有一點我確實是欺騙了我的客人,我並不是真的能把所有想說的話都能傳遞給對方的,有時候,我只能夠傳遞一點兒的概念出去。這就是這個宇宙奇妙之處,這個宇宙太大,也有太多不同的能量,能否連結在一起或者能否傳遞任何信息,真的除了看緣份之外,我都不能解釋什麼。當然這些事,我並不會告訴給我的客人,很多時候知道的事越少越幸福。能夠把希望帶給客人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能夠帶點安慰給還活着的人,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她的信上寫着:“阿宏,好久不見了,你最近好嗎?問你這一句話好像有點荒謬,一向樂觀的你無論在哪裡都一定能夠發現好的事物的,對不對?我還是老樣子,不想唸書,不想工作,不想和任何人相處,但你知道嗎?有一句話我一直埋藏在心裡很想和你說,那就是‘謝謝你’!我是真的很感激當年你為我所做的一切,你也是我當年在學校唯一的快樂來源。我有着一半的白人血統,所以膚色和其他同學不一樣,他們總覺得我臉色蒼白得像魔女一樣。我也就是這樣成為了被欺負的對象,幸好有你一直陪在我身邊,一直幫我出頭,甚至幫我承擔了一些本來是由我所承擔的責任。當年你在男童院被襲擊而導致身亡的事,我到現在還是內疚得很。現在我只是希望你在另外一個世界能夠快樂,也能夠得到一直以來你所嚮往的自由。”信的結尾寫着:“一直會以另外一種方式愛你的善柔。”唸完這封信後,我的內心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因為信中的那兩個人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學。
我放下眼前的這封信,回想起在我的高中時期,真的有一個叫做董以宏的男同學和一個叫做陳善柔的女同學。我也依稀地記得,以前因為善柔有一雙藍藍綠綠的大眼睛和一身完全沒有半點血色的肌膚,很多同學都恥笑她長得很可怕,像魔女一樣,很多同學都喜歡作弄她。那個時候,我也是打從心底裡覺得她是一個魔女,但我有這種感覺並不是因為她的外表,而是她的氣質,她身上的確會散發出一種讓人害怕的氣息。一直以來,她像是一個沒有任何情感的人,就如同那天她來到我的店舖,我覺得她像一個活生生但沒有靈魂的洋娃娃一樣。那天她應該是配戴了彩色隱形眼鏡,我記得她的雙眼應該是咖啡色的,並不是從前那雙藍藍綠綠的大眼睛,所以我一時聯想不到她們竟然是同一人。
那年,阿宏因為傷人罪被判了入男童院。當時,沒有任何人知道事實的真相。只是謠言滿天飛,有人嘲笑善柔是一個吸血鬼,而阿宏是為了保護善柔所以才傷人的。阿宏入了男童院沒多久後,善柔退了學。善柔本來的朋友就不多,可以說是她是除了阿宏之外,並沒有任何能夠交心的朋友。她退學後,根本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也沒有人嘗試要找她。隨着時間逝去,同學們都忙着自己的生活,漸漸地把阿宏和善柔這兩個人忘記,就好像他倆從來沒有出現過似的。如今,我讀了這封信之後,高中時期的往事重新在我腦海中上演一次,一切依然歷歷在目。
阿宏是個典型的陽光男孩,是學校的籃球隊隊長,是老師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是眾女生夢寐以求的理想對象。相反,善柔像是一個邊緣人,她成績不好,和同學們的關係也常常處於繃緊的狀態。善柔在小息的時候,總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操場的角落,她那雙藍綠的大眼睛沒有焦點地看着前方。我深信如果並不知道她是誰的話,大概真的會被她嚇倒,她真的就像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安靜地守候着獵物一樣。
有一天,阿宏剛練完球,他手上拿着兩瓶水慢慢地走向善柔的方向。當時在操場上的每一個人都目不轉睛地看着這一幕,每個人都在想為什麼萬人迷會和這個魔女有關係。
阿宏把其中一瓶水交給善柔,然後坐在她身旁。他用溫柔的眼神凝望着善柔,善柔露出幸福的微笑,他倆的周圍瀰漫着浪漫的氣氛。隔天,整個學校都傳出他們倆在交往的消息。
突然間,善柔這個邊緣人成為了眾人的敵人,好像她搶走了別人所期待的一切。欺負善柔的人變本加厲,把她的書包收起來,把垃圾放在她的桌子上,把她的椅子弄髒,更過分的是有人把口水吐進她的午餐裡,還恥笑她說:“魔女不用吃飯的,你繼續去吃人類吧。”說完,那幾個女生便假裝害怕地大叫,然後跑走。現在我回想起來,便覺得其實當時也許善柔並不是異類,只是一切的欺凌都出自於人們本身的嫉妒心。從前我便這樣覺得,撇除她那怪異的氣質,讓人感到有點畏懼之外,其實善柔確實是一位美人胚子,這也難怪阿宏會喜歡上她。一開始是她的美貌讓別人妒嫉,之後是她成為了阿宏的女友,讓其他人更加憎恨她。
我開業的第一天曾經告訴過自己,千萬不要理會客人的私事,只是把他們的說話傳遞出去便可以了。現在我違反了自己的職業操守,但仍然忍不住撥打了電話給善柔,我想和她表明我就是他們以前的高中同學。我想了解清楚當年發生了什麼事。電話接通的那一刻,我鼓起勇氣說:“善柔,我已經嘗試把你想對阿宏說的話傳遞給他。”
“你偷看了我的信。”她用責怪我的語氣說道。
“你誤會了,我本來就是要先把信件讀完,才能替你把話傳遞出去,但我打這通電話給你是因為我想和你坦白,我是你的高中同學,我想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電話的另一端安靜了幾秒,才輕聲說:“就是他為了保護我,所以才傷人的。”
“我想知道阿宏之後在男童院又發生了什麼事?”
善柔沉默了一陣子,說:“我過來你的店舖再說。”
這時坐在我對面的善柔,並沒有配戴彩色隱形眼鏡,我看着她那雙藍綠色的眼睛便彷彿回到了我們的高中時期。當年,我沒有欺負或嘲笑過善柔,但也沒有在她被欺負的時候幫助過她。如今,我面對着她,感到有點內疚。說到底,大家都心知肚明,她並不是魔女更不是吸血鬼,她只是一個混血兒,而且長得很漂亮。因為她的美貌惹來別人想要貶低她,而讓自己內心好過點。
善柔那雙藍綠的大眼睛盯着我的雙眼說:“其實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我便覺得你有點面熟,但畢竟我和以前的同學沒有聯繫,我也不好意思和你相認。”
“當時你配戴了咖啡色隱形眼鏡,所以我認不出你是善柔。”我尷尬地說。
“你說你想知道更多關於我和阿宏的事,你想知道什麼?是否能夠幫助我更加清晰地和他溝通?”
“抱歉,其實你想我傳遞的話,我已經嘗試傳遞給他了,但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次傳遞上出了點問題,好像怎樣連結也連結不到他。平常死去的人仍然會有一種能量在這世上,我只要能連結這能量便能與他們溝通,但這次,我真的聯繫不上。我會再不斷嘗試,如果還是不行的話,我會把錢退給你。”我老實地向善柔說出我的難處,這也是我第一次和客人這麼坦白。以前就算我不能把全部信息傳遞出去,但至少會多少傳遞一點兒。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我完全不能連結到阿宏的能量,那就是代表我半點兒的信息也不能傳遞給他。
自從上次見完善柔之後,無論我再怎樣努力也連結不到阿宏,但一切就像在冥冥之中總有安排。那天,我出門前,看到鄰居帶着小孩想要拿包裹去寄。我們的關係是很不錯的,他們知道我自己一個住,很多時候都會煮多一點飯菜送過來給我。我在他們的門前看到小孩在耍脾氣,吵着說不想出去。當時,那位媽媽手忙腳亂地想要一手牽好小孩,一手拿好包裹。我便主動向她提議,我可以幫她把包裹拿去寄,一開始她有點不好意思,但小孩不停地吵鬧,她只好尷尬地答應了。
因為要寄包裹的緣故,我走到一條陌生的街道上,看見了一間以前沒有見過的咖啡店。那間小小的咖啡店,裝修簡單,只是在四面的牆上油上了白色的油漆,也沒有多餘的裝飾,那樣簡單的風格正是我喜歡的模樣。我把包裹拿去寄後,便走進這間咖啡店。我找了一個靠近窗戶的位置坐下來, 外面人來人往的街道更顯得咖啡店內的寧靜十分可貴。我向店員點了一杯咖啡,便無聊地坐在椅子上,欣賞着這一刻的平靜。有一位高大的男生背影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正在為我準備我的咖啡。當他轉過身來,想把咖啡遞給我的時候,我便一眼把他認出來,一個從小便這麼觸目的人,怎麼可能會認不到? 我驚訝地看着眼前的他,他便是阿宏。
阿宏露出燦爛般的笑容對着我說:“好久不見了,你還認得我嗎?我是你的高中同學,阿宏。”我一時不懂得怎樣反應,只是有點不知所措地點了點頭。阿宏說這間咖啡店是他幾年前開的,算不上是什麼大生意,但也算是賺到了一點生活費。他並沒有提及他以前進男童院的事,畢竟那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不願意提起也是人之常情。他不願意回憶起,我也不好意思問。只是我感到非常疑惑,為什麼善柔會以為他已經不在人世了。我終於鼓起勇氣問阿宏:“你還記得善柔嗎?我記得之前你們好像交往過。我前一陣子碰見過她,她好像不太清楚你的近況。”阿宏聽到善柔的名字後,面色一沉。過了好一陣子才開口問:“她最近好嗎?”
“她應該過得不錯。之前她跟我說過她很感謝你。”我回答道。
“以前我做了一些對不起她的事,我一直很擔心她會過得不好。”說完, 他便繼續去煮咖啡,沒有再向我透露些什麼。
我拿起手機致電給善柔,告訴她我已經聯絡到了阿宏。善柔出乎意料地冷靜,她跟我說:“其實一切都不重要了。那些話與其說是說給阿宏聽,那倒不如說是我想說給自己聽。”她說着這一切的時候,我突然間才明瞭,其實一直以來她是知道真相的。我覺得自己被耍了,她明知道阿宏還在這世上,為什麼卻要來找我?我帶點生氣地質問她:“你是知道阿宏還生存着的,對不對?”
電話傳來一陣顫抖的哭聲說:“當年,阿宏想和我分手,我接受不了他想要和我分手的這個事實,便欺騙他說我有了他的小孩。當時,有一個同學在廁所的垃圾桶,看到我的驗孕棒是陰性的。她喜歡阿宏,她想去找阿宏拆穿我的謊言,我為了阻止她,便用一根在學校隔壁空地找到的鐵管,把她打傷了。那個時候,我只知道我不能讓她破壞我的計劃,所以我用盡全力地毆打她。那時,她有兩條肋骨被我打斷了。我就這樣把她遺留在空地上,直到隔天有人經過空地才發現她,把她送去醫院。幸好,她沒有生命危險。那天早上,我用木棍把自己打傷,然後哭着去找阿宏,說那個女生知道我懷了他的孩子,而引起了她的妒忌心。我騙阿宏是她攻擊我,我才還手的。阿宏看在小孩的份上,幫我頂了罪,他也因為這樣而進了入男童院。”
“因為你根本不想去面對,你根本不想和他正式道歉,害怕跟他坦白這一切,所以你情願相信他已經死亡了。你覺得對着死去的人,便能一直持着那種矜貴的姿態。就像是那種你感到很抱歉,只是他已經不在人世,無能為力的你不能再做什麼,你便能成功地把自己變成了那個最無辜的受害者,對吧?”
“我直到現在也覺得自己沒有錯。如果當初阿宏不是想和我分手的話,我根本不會走到這一步,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他現在已經得到了他的報應,我也放下了他曾對我做過的傷害。”
“你用愛之名傷害了愛你的人,阿宏是因為愛你們的孩子才這樣保護你的。”
“如果他愛我的話,他就不會和我分手。我恨不得他當初真的在男童院內被人襲擊致死。所有不愛我的人都是活該的,就像當年那個想要拆穿我的女同學一樣,他們都是活該被懲罰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感到毛骨悚然。果然,她最初給我的感覺是沒有錯的,善柔確實是一個只有美麗外表但沒有情感、沒有靈魂的可怕洋娃娃。
賴 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