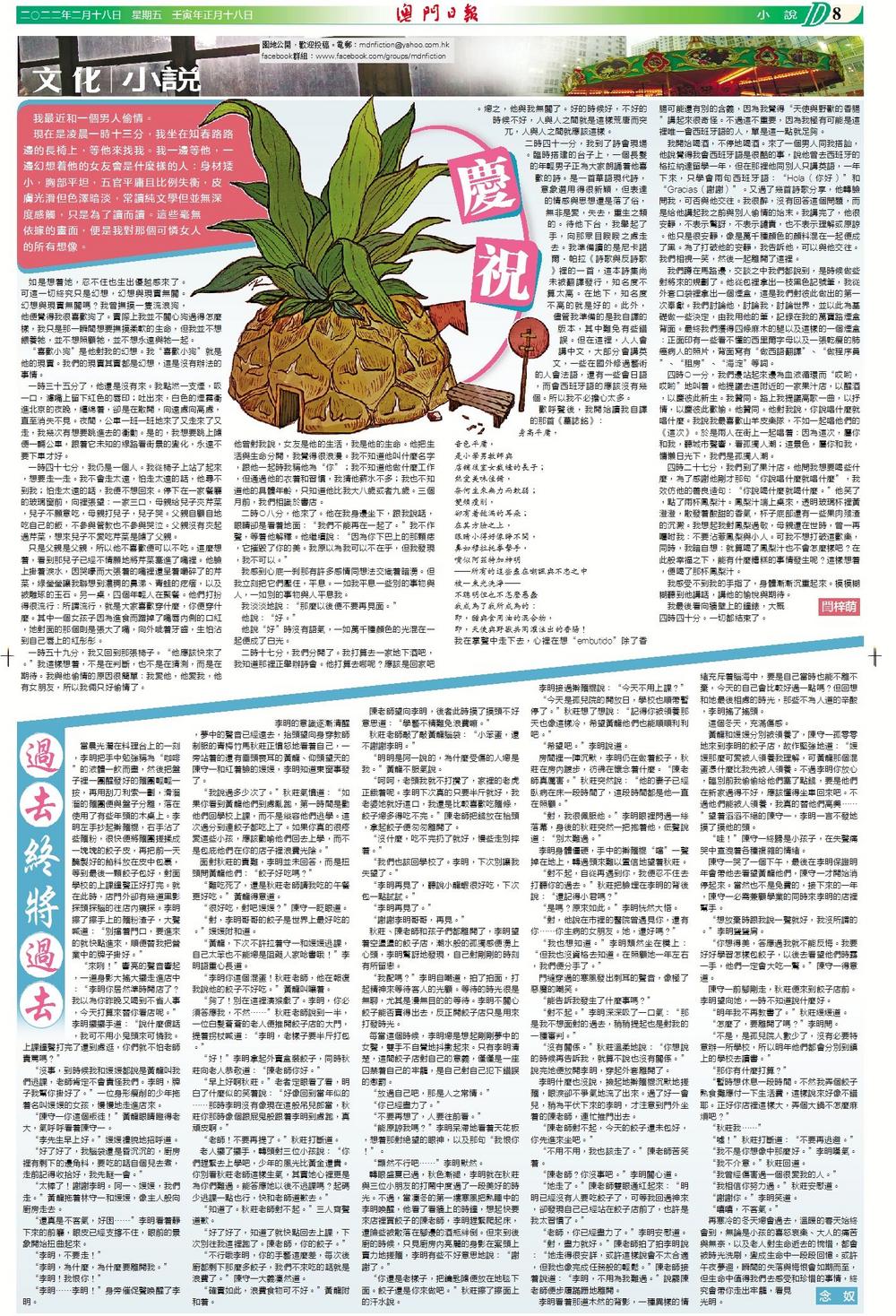慶祝
我最近和一個男人偷情。
現在是凌晨一時十三分,我坐在知春路路邊的長椅上,等他來找我。我一邊等他,一邊幻想着他的女友會是什麼樣的人:身材矮小,胸部平坦,五官平庸且比例失衡,皮膚光滑但色澤暗淡,常讀純文學但並無深度感觸,只是為了讀而讀。這些毫無依據的畫面,便是我對那個可憐女人的所有想像。
如是想着她,忍不住也生出優越感來了。可這一切終究只是幻想,幻想與現實無關。幻想與現實無關嗎?我曾撫摸一隻流浪狗,他便覺得我很喜歡狗了。實際上我並不關心狗過得怎麼樣,我只是那一瞬間想要撫摸柔軟的生命,但我並不想餵養牠,並不想照顧牠,並不想永遠與牠一起。
“喜歡小狗”是他對我的幻想。我“喜歡小狗”就是他的現實。我們的現實其實都是幻想,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一時三十五分了,他還是沒有來。我點燃一支煙,吸一口,濾嘴上留下紅色的唇印;吐出來,白色的煙霧衝進北京的夜晚,纏綿着,卻是在散開,向遠處向高處,直至消失不見。夜間,公車一班一班地來了又走來了又走,我幾次有想要跳進去的衝動。是的,我想要跳上隨便一輛公車,跟着它未知的線路看街景的變化,永遠不要下車才好。
一時四十七分,我仍是一個人。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想要走一走。我不會走太遠,怕走太遠的話,他尋不到我;怕走太遠的話,我便不想回來。停下在一家餐廳的玻璃窗前,向裡張望:一家三口,母親給兒子夾芹菜,兒子不願意吃,母親打兒子,兒子哭。父親自顧自地吃自己的飯,不參與管教也不參與哭泣。父親沒有夾起過芹菜,想來兒子不愛吃芹菜是隨了父親。
只是父親是父親,所以他不喜歡便可以不吃。這麼想着,看到那兒子已經不情願地將芹菜塞進了嘴裡。他臉上掛着淚水,因哭嚎而大張着的嘴裡還呈着嚼碎了的芹菜,綠瑩瑩讓我聯想到濃稠的鼻涕、青蛙的疙瘩,以及被雕琢的玉石。另一桌,四個年輕人在聚餐。他們打扮得很流行:所謂流行,就是大家喜歡穿什麼,你便穿什麼。其中一個女孩子因為進食而蹭掉了嘴唇內側的口紅,她對面的那個則是張大了嘴,向外呲着牙齒,生怕沾到自己唇上的紅彤彤。
一時五十九分,我又回到那張椅子。“他應該快來了。”我這樣想着,不是在判斷,也不是在猜測,而是在期待。我與他偷情的原因很簡單:我愛他,他愛我,他有女朋友,所以我倆只好偷情了。他曾對我說,女友是他的生活,我是他的生命。他把生活與生命分開,我覺得很浪漫。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跟他一起時我稱他為“你”;我不知道他做什麼工作,但通過他的衣着和習慣,我猜他薪水不多;我也不知道他的具體年齡,只知道他比我大八歲或者九歲。三個月前,我們相識於書店。
二時○八分,他來了。他在我身邊坐下,跟我說話,眼睛卻是看着地面:“我們不能再在一起了。”我不作聲,等着他解釋。他繼續說:“因為你下巴上的那顆痣,它摧毀了你的美。我原以為我可以不在乎,但我發現,我不可以。”
我感到心底一刹那有許多感情同想法交織着暗湧。但我立刻把它們壓住,平息。一如我平息一些別的事物與人,一如別的事物與人平息我。
我淡淡地說:“那麼以後便不要再見面。”
他說:“好。”
他說“好”時沒有語氣,一如萬千種顏色的光混在一起便成了白光。
二時十七分,我們分開了。我打算去一家地下酒吧,我知道那裡正舉辦詩會。他打算去哪呢?應該是回家吧。總之,他與我無關了。好的時候好,不好的時候不好,人與人之間就是這樣荒唐而突兀,人與人之間就應該這樣。
二時四十一分,我到了詩會現場。臨時搭建的台子上,一個長髮的年輕男子正為大家朗誦着他喜歡的詩。是一首華語現代詩,意象選用得很新穎,但表達的情感與思想還是落了俗,無非是愛,失去,重生之類的。待他下台,我舉起了手,向那眾目睽睽之處走去。我準備讀的是尼卡諾爾 · 帕拉《詩歌與反詩歌》裡的一首,這本詩集尚未被翻譯發行,知名度不算太高。在地下,知名度不高的就是好的。此外,儘管我準備的是我自譯的版本,其中難免有些錯誤。但在這裡,人人會講中文,大部分會講英文,一些在國外修過藝術的人會法語,還有一些會日語,而會西班牙語的應該沒有幾個。所以我不必擔心太多。
歡呼聲後,我開始讀我自譯的那首《墓誌銘》:
身高平庸,
音色平庸,
是小學男教師與
店舖後室女裁縫的長子;
熱愛美味佳餚,
奈何生來無力而軟弱;
雙頰瘦削,
卻有着飽滿的耳朵;
在其方臉之上,
眼睛小得好像睜不開,
鼻如穆拉托拳擊手,
嘴似阿茲特加神明
——所有的這些盡在嘲諷與不忠之中
被一束光洗淨——
不聰明但也不怎麼愚蠢
我成為了我所成為的:
即,醋與食用油的混合物,
即,天使與野獸共同灌注出的香腸!
我在掌聲中走下去,心裡在想“embutido”除了香腸可能還有別的含義,因為我覺得“天使與野獸的香腸”講起來很奇怪。不過這不重要,因為我極有可能是這裡唯一會西班牙語的人,單是這一點就足夠。
我開始喝酒,不停地喝酒。來了一個男人同我搭訕,他說覺得我會西班牙語是很酷的事,說他曾去西班牙的格拉納達留學一年,但在那裡他同別人只講英語,一年下來,只學會兩句西班牙語:“Hola(你好)”和“Gracias(謝謝)”。又過了幾首詩歌分享,他轉臉問我,可否與他交往。我很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給他講起我之前與別人偷情的始末。我講完了,他很安靜,不表示驚訝,不表示譴責,也不表示理解或原諒。他只是很安靜,像是萬千種顏色的顏料混在一起便成了黑。為了打破他的安靜,我告訴他,可以與他交往。我們相視一笑,然後一起離開了這裡。
我們蹲在馬路邊,交談之中我們都說到,是時候做些對將來的規劃了。他從包裡拿出一枝黑色記號筆,我從外套口袋裡拿出一個煙盒,這是我們對彼此做出的第一次奉獻。我們討論他,討論我,討論世界,並以此為基礎做一些決定,由我用他的筆,記錄在我的萬寶路煙盒背面。最終我們獲得四條麻木的腿以及這樣的一個煙盒:正面印有一些看不懂的西里爾字母以及一張乾瘦的肺癌病人的照片,背面寫有“做西語翻譯”、“做程序員”、“租房”、“海淀”等詞。
四時○一分,我們邊站起來邊為血液循環而“哎喲,哎喲”地叫着。他提議去這附近的一家果汁店,以醒酒,以慶彼此新生。我贊同。路上我提議高歌一曲,以抒情,以慶彼此歡愉。他贊同。他對我說,你說唱什麼就唱什麼。我說我最喜歡山羊皮樂隊,不如一起唱他們的《這次》。於是兩人在街上一起唱着:因為這次,屬你和我,聽城市聲響,看孤獨人潮;這景色,屬你和我,慵懶日光下,我們是孤獨人潮。
四時二十七分,我們到了果汁店。他問我想要喝些什麼,為了感謝他剛才那句“你說唱什麼就唱什麼”,我效仿他的善良造句:“你說喝什麼就喝什麼。”他笑了,點了兩杯鳳梨汁。鳳梨汁端上桌來,透明玻璃杯裡黃澄澄,散發着酸甜的香氣,杯子底部還有一些果肉殘渣的沉澱。我想起我對鳳梨過敏,母親還在世時,曾一再囑咐我:不要沾惹鳳梨與小人。可我不想打破這歡樂,同時,我暗自想:就算喝了鳳梨汁也不會怎麼樣吧?在此般幸福之下,能有什麼糟糕的事情發生呢?這樣想着,便喝了那杯鳳梨汁。
我感受不到我的手指了,身體漸漸沉重起來。模模糊糊聽到他講話,講他的愉悅與期待。
我最後看向牆壁上的鐘錶,大概四時四十分。一切都結束了。
閆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