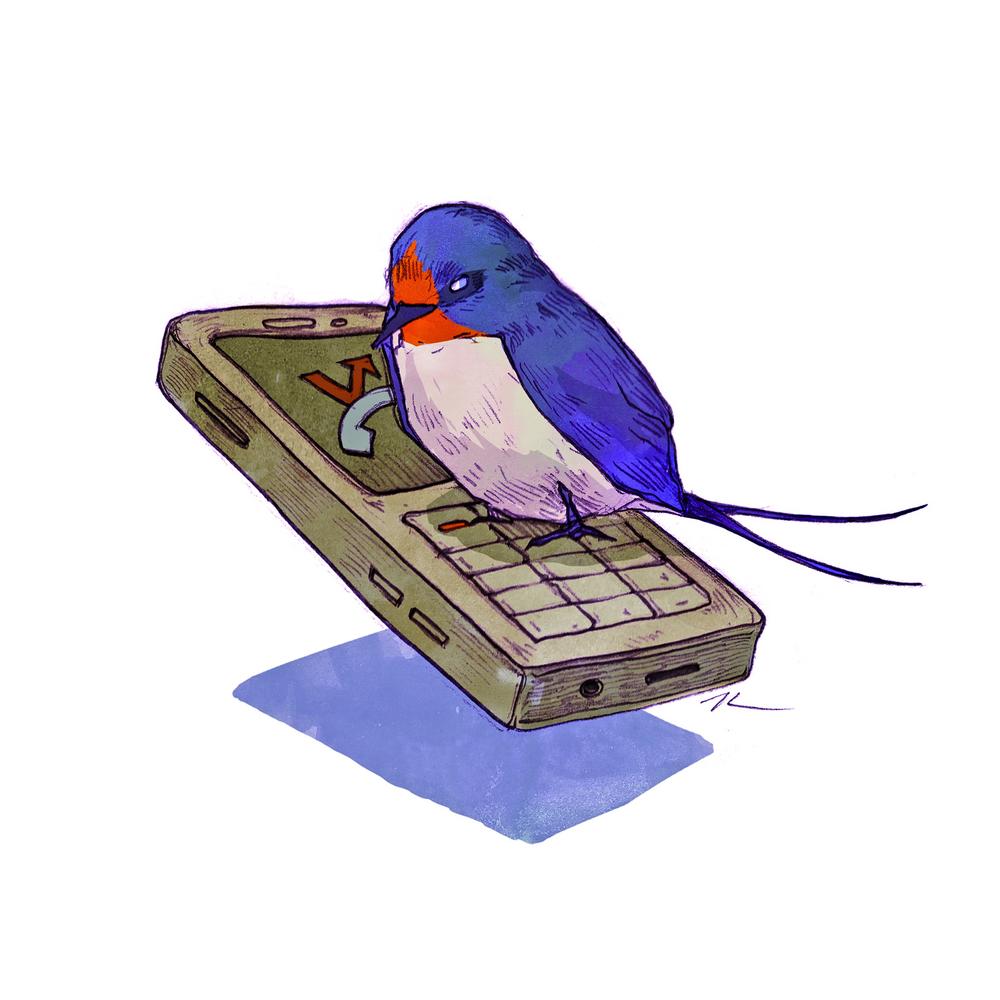唯親
阿幸焦躁地看着迤邐山路,腸胃不停絞痛,但他清楚這不是吃壞肚子。音樂一首切過一首,從輕快到電音,沒有一首符合心意。黑壓壓的山路如同巨大魔獸的腸道,即使明亮的鹵素大燈也照不到盡頭,阿幸血仇似地重踩油門,然後在轉彎處急剎,每一下都痛擊腸胃,但彷彿不趕快離開這裡,就會被魔獸的胃酸腐蝕。
好不容易開到筆直的公路,兩側明亮的路燈才讓阿幸覺得舒服一些。他的精神狀況不好,昨晚才陪一位大老闆應酬到深夜,接着又撐着發痛的腦子陪一組客人看房。身為金牌地產,從新人時期拿過新人業務冠軍開始,就一直是分店的常勝軍,他嘴甜業務能力強,別人說不清楚的,他總是能交代得明明白白,難纏的客戶總能被他治得服服貼貼。
即使到除夕前一日依然忙得不可開交,最後一組客人滿意地從一坪八十萬的豪宅離去,阿幸才匆忙回家整理行李,開着那輛保養如新的奧迪上路。一早到現在,他除了等客戶時去便利商店偷閒買個飯糰果腹外,也只多喝三杯咖啡。
剛上高速公路,阿幸便感到胃部熱辣辣翻騰,他想起醫生耳提面命一定要按時吃飯,少碰煙酒,但誰不是為五斗米將身體折騰得千瘡百孔?更何況阿幸每個月的獎金可不只五斗米。
阿幸找了休息站休息,在背包裡翻出胃藥,囫圇嚥下。等胃部稍微消停,他忍不住抱怨起這趟旅程。不對,這是每年必經的地獄之旅。從雲蒸霞蔚的大都會回去崇山峻嶺的鄉下,好山好水好無聊,但比起一成不變的山脈與海岸,阿幸有更厭惡、更抗拒的東西,那些事物總會在夜裡的山路具現成可怕的魔獸。
終於車燈照亮寫着家鄉名字的指示牌。總算到了,他暗暗抱怨每次回鄉一趟堪比唐三藏取西經,倒不是這條路真的有九九八十一難,而是他得跨越心裡的障礙。
“阿幸哥哥回來啦。”村子不大,號稱燈廠的奧迪一下照亮山村。負責喊話的是堂哥的小兒子,才剛三年級。
如同往年,親戚們在門口擺了三大桌,此時小孩子都爭先恐後跑出去迎接。大家都知道,只要阿幸回來,紅包一定不會少。
儘管阿幸很累,但再疲憊都能擠出令人滿意的笑容,才是他成為銷售冠軍的不二法門。大大小小只要還在讀書的一律有紅包拿,其中最厚的一個遞給了身為大家長的祖母,稱讚聲此起彼落,歡聲不斷。
“幸仔,來跟阿伯喝一杯。”坐在靠客廳那桌的中年人醉醺醺喊道。他們桌邊已經擺了一圈高粱空瓶。
阿幸聽見招呼聲,頓時眼神流露一絲不快,但隨即又擺出職業級笑容。高粱與水三比七,舉杯角度不卑不亢,欣喜地說:“爸,各位叔叔伯伯,我先乾為敬,你們隨意。”
接着昂頭一杯,辣氣衝喉,阿幸甩了甩杯子,直上半杯純高粱,一口恭賀新禧,一聲萬事如意,五十八度的酒毫無保留熱辣辣地直奔腸胃。
一眾叔伯紛紛叫好,大伯拍手道:“難怪人家是銷售冠軍,氣魄就是不一樣。梁家都靠幸仔啦。”
大伯年近六十,留長馬尾,精細修剪的小鬍子,穿花襯衫,儼然有質感的老藝術家做派。說話間,大伯不甘示弱也純飲半杯。
“那是大伯不棄嫌。”
“年輕人還是要跟你多多學習啦。來,大家敬一下。”阿幸的父親大笑道。
“關於那塊地的事情——”
“沒規沒矩,現在先別說這個,來,再敬一杯。”滿臉通紅的父親牛飲而盡,博得滿堂彩,但阿幸記得年前才看見父親傳來一張肝指數過高的診斷報告。
可是無人能制止這個頂着如懷胎十月啤酒肚的大塊頭,說到喝酒五頭牛都拉不走。
阿幸用奉承的笑臉隱藏鄙夷,那些愁緒化作酒水,跟着發痛的胃一起糾結。大伙聊起阿幸這幾年如何了不得,在大都市買車買房,結交都是上流富豪,把他們姓梁的都沾得顏面有光。
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叔伯阿姨都希望阿幸好好照顧弟弟妹妹們。
阿幸一邊替大家斟酒,一邊滿口答應,他酒量沒有這麼好,剛剛幾杯烈酒已讓他感到頭昏,再喝恐怕就要倒地不起。不過應酬了這麼多次,阿幸早對如何擋酒並讓客人開心服貼了然於胸。
只是父親永遠是掌握不住的炸彈,喝開了後一直命令阿幸喝,幸虧向來說話風趣的大伯打了圓場,但圓不了阿幸對父親的憎恨,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若輪迴果報存在,阿幸認為自己肯定欠了父親好幾世的債,這輩子才會出生當他兒子。
儘管心裡憤怨,阿幸仍然笑臉迎人,這是他多年業務磨練出來的反射動作,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幾乎客戶都吃這一套。只是他那個嗜酒如命、一沾酒就作怪的父親,就跟那些刁鑽酒品差的客戶一樣,不只強迫喝酒,還要用自己的人生經驗教育阿幸,不時還要發個酒瘋,旁人怎麼勸都沒有用。為了生活,阿幸咬着牙笑一笑便過去了,唯獨對父親不行,看着那張老臉,天知道阿幸多想甩一個酒杯過去。
終於在大伯的斡旋下,深夜時酒局散去,大伯特意留下阿幸,要來個兩人深談。大伯遞了根煙給阿幸,此時新月光澹,村子到山頭一片黑壓壓,只有棚頂的鹵素燈提供光明。
兩人夾着煙,阿幸知道大伯要說什麼,但尚不是主動開口的時機。沉默了一會,大伯抖掉煙灰,語重心長地說:“幸仔,那塊地可能沒有辦法給你。你先聽大伯解釋好嗎?”大伯察覺到阿幸的眼神瞬間變異。
阿幸吸了口煙,點頭,沒有做出多餘表情。
“那塊地是你阿公很早就分給你爸了,但你知道你爸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愛喝酒,喝了酒就沒有判斷能力,又不懂理財,所以常常為了義氣相挺借錢,沒有一筆收得回來。”
阿幸贊同大伯的說法,因為母親當年為這個理由家庭革命了無數次,最後才受不了離婚遠去,後來大概看破紅塵,到了一家小佛寺剃度為尼,阿幸一年也只有一次以禮佛為由見上一面。阿幸一開始很錯愕,以為母親想不開,可是在佛寺裡看見母親神情安然,不像從前成天苦瓜臉,似乎世上煩憂都已拋在山門外,那一刻阿幸明白母親焦躁多年的心已找到歸屬,之後都喚她方明法師。
相較母親的解脫,父親像是打算一生浮沉。
“你爸欠的錢,是我跟你三伯、五叔一起還的。”
聽到這裡,阿幸已了然,父親興高采烈說得把祖厝地傳給他不過是一廂情願,可是對這個發展阿幸並不意外。
“我明白,是我爸惹的禍,如果這塊地能償清他欠下的,我沒有意見。”阿幸心裡早對祖厝地不抱寄望,其實這次回來也是打算跟幾位叔伯把事情講清楚。
“你阿公對你爸最好,幾乎最好的家產都留給他,可是他……幸仔,你爸是好人,只是不是個稱職的父親。”
“我知道,所以他才幫二伯作保,迫得我媽跟他離婚。但我媽已經看透了,我的事業也很順利,過去的就算了,再提也沒有意思。”
說起阿幸的二伯,從小就到處打架鬧事,長大後吃喝嫖賭樣樣精通,在外面亂投資欠了一堆錢,求父親作保跟高利貸借錢,自己就不曉得跑哪去,父親被高利貸迫得把祖厝地貸出去還,大伯、三伯、五叔則湊錢買回來,當然這件事是阿幸成年後知道的。阿公臨終前還一直要父親把地守好,百年後傳給阿幸。
大家看到二伯的時候,是在一家戒毒中心,當時他形容枯槁,像一條乾瘪的蟲,怎麼看都不像個人,沒有多久便死去。對於二伯的死,阿幸沒有多大感覺,倒是父親哭得死去活來。
阿幸跟大伯抽了幾根煙,各自回房。阿幸睡在小時候的通鋪,多年來屋內一樣老舊,如同往年,那一床紅花被褥早已擺好。房間裡兒時味道依舊,在這裡會想起哄他午覺的母親,還有每個夜裡傳來父母的爭吵聲。
阿幸走到外頭的浴室盥洗,磁磚地還是一樣佈滿水垢,門鎖仍是壞的,裡面的人只能用鐵絲綁住鎖扣,但並不牢靠。小時候他最喜歡跟堂哥一起整堂弟,只要兩人用力一拉,就能扯開浴室門。
浴室裡唯一的新物件是三年前更新的熱水器,舊的燒個五分鐘就會漸漸沒有熱水,別妄想在裡面悠閒地沖澡。而且重燒一次水得等上半小時,要是沒有抓好時間,下一個進去就得在寒冷的冬天洗冷水。他跟堂哥常常這樣整堂弟。
阿幸脫下上衣,鏡子裡他的胸前有一道疤痕,每次看到這道醜陋的疤,平靜的心便會有所波盪。小學四年級,父親剛替二伯作保後三個月,高利貸整天來家謾罵潑漆撒冥紙,後來有一晚來了幾個沒見過的兇神惡煞,這次討得更狠,還拿出小刀威嚇,父親被一頓胖揍,躲在屋裡的阿幸衝了出去想護住父親,拉扯中不慎被劃上一刀。
所有人頓時驚呆,討債的立刻一哄而散,大伯則開車送阿幸去急診,幸而傷口不深,只是留下一道無法消除的疤痕。事後砍傷人的被警察抓進去蹲,這事件變成傾軋父母婚姻的稻草。那時母親帶阿幸走,直到初中畢業前都沒再回過老家。
母子獨在外地漂泊,生活艱辛,期間父親一分錢也沒有寄來,全仰賴大伯等人接濟,阿幸才不必半工半讀,得以完成學業。這份情阿幸感念不忘,因此儘管祖厝地被政府劃成新城重劃區後翻漲十倍,阿幸也認為這些遠不夠償還當時之恩。母親出家前一直心心念念阿幸能繼承祖厝地,每每說到阿幸的傷疤,便暗暗流淚。要不是接觸佛法,母親恐怕一生都要困入孽債循環無法自拔。
回老家三天,阿幸獲得難得的清閒,腸胃問題似乎也在正常作息中緩解,甚至萌生了要在這山清水秀之地買一處田園等退休後隱居。但他刻意與父親避不見面,兩人如陌生人般點頭寒暄,無法認真說上幾句話,他知道父親有話要說,但他們之間的隔閡如同他胸前的疤無法抹去。父親不喝酒時沒有這麼多脾氣,見阿幸不肯多說話,也不強迫。
初三清晨,阿幸告別大伯,回去繼續繁忙地工作。隨着他在公司的地位日益重要,應酬數都數不過來,連醫生都直搖頭。阿幸這些年賺的錢普通人一輩子都賺不來,現在的阿幸不是因為缺錢才拼命幹,他總是會想到剛跟母親搬出老家時,母親的存款全用在搬家跟租房上,已經所剩無幾,因此只能買一個便當給阿幸,自己則白飯混肉汁吃,阿幸那時正在發育,有時一個便當還不夠,可是他還是刻意說吃不了這麼多,將肉留給母親。
有次母親工作的小工廠延遲發薪,那時勞工保障還不完善,母親硬是用一包冷凍水餃煮成四天份,這也讓阿幸徹底怨恨父親。一直到大伯好不容易聯繫上他們,給了經濟援助才好轉。因此阿幸害怕窮,即使身體出了問題還是努力工作。
父親打來電話好多次,但阿幸沒有接,有時是因為忙碌,有時只是靜靜等到手機靜止。天氣越來越熱後,阿幸的腸胃問題越發嚴重,他在一場宴會回去途中,竟在計程車上昏迷,被司機送到醫院,醫生看了檢查報告,苦口婆心勸阿幸暫停工作,現在是因為勞累過度加上胃潰瘍導致昏厥,再嚴重下去可能就會變成胃癌。
阿幸左思右想,最後接受醫生的建議,並告訴老闆這件事。雖然老闆捨不得讓阿幸休息,可是考量他的身體狀況,同意讓他先休養三個月再看情況。沒事幹的阿幸只能成天待在家裡,當了這麼多年工作狂,一時間閒下來很不習慣,沒事只能上健身房鍛煉,去河堤跑步。
這時他意識到父親有好一段時間沒有打來,他忖閒着也是閒着,不如回老家看看情況。久違地撥通父親的號碼,那頭卻無人接聽,連續幾通都是如此,這倒很新奇,因為阿幸很少主動打過去,因此父親從來沒有漏接過。
但阿幸沒有多想,只是等父親回撥,卻等到陌生來電,他忖多半是股票推銷,因此不去理會。可是同一個號碼打來四次,他忖不可能是某個客戶的來電,因為他早跟老客戶們說明休養三個月的事。
阿幸揣着好奇心撥回去,另一頭傳來熟悉的聲音。
“幸仔,你終於接了。”
“大伯?”
阿幸並沒有儲存親戚的聯絡方式,一直以來也沒有親戚打給他,大家都是過年那幾天短暫見面。阿幸頓時感到不妙。
“你爸住院了,趕快找時間回來看看。”
“怎麼回事?”
“他之前有打給你,不過你大概工作太忙沒有時間接,但他這次太嚴重了,所以我只好從他手機找你的號碼打給你。”
“我知道了。”阿幸掛掉電話,連忙搭最近一班的高鐵。
阿幸忖父親大概是喝酒喝出問題。趕到醫院時,他見到大伯跟堂哥,大伯說父親早上上廁所時暈倒,撞破腦袋。阿幸才知道父親上個月開始出現腦溢血的症狀,所以才不停打給他。
進到單人病房時,他看見父親雄壯的身軀居然消瘦了一大圈。父親坐在病床上,呆滯地盯着窗外。
大伯悄聲提醒道:“他現在狀況不太好。”
阿幸頷首,輕聲叫着父親:“你還好嗎?”
“你是誰?”父親疑惑地盯着阿幸,嘴角完全合不攏,因此說話相當含糊。
“我是阿幸啊。”
“我兒子,也叫阿幸。”
阿幸急忙看向大伯,大伯皺眉解釋道:“你爸上個月開始就常忘東忘西,後來又突然中風,那時候我就想打給你,但你爸說你在忙不能接電話,要不是這次很危急……醫生說這次撞擊可能讓他記憶變得更差,雖然他還認得我,但……幸仔,你跟你爸好好聊一下。”
大伯跟堂哥出去後,病房裡剩下阿幸跟父親乾瞪眼。
“我兒子,阿幸,也在醫院,不過已經出院了。”父親緊緊捏着虎口,不利索地說:“因為我欠錢,害他被砍一刀,我對不起他。我不能回家,在醫院,沒辦法,幫他蓋被子,他很調皮,會踢被子。”
“爸……”阿幸好多年未喊過一聲“爸”。
但父親沒有聽見,喃喃自說自話,記憶開始胡亂跳動,“我要趕快出院,賺錢還錢,不能讓阿幸受苦。他媽媽,很辛苦,因為,我。不要怪二哥,二哥最疼我,我被欺負二哥幫我,沒有錢二哥給我……”
說着,父親不禁淚眼婆娑。
直到父親病逝前,依舊沒有想起阿幸是誰,阿幸看着父親的棺木被送入火化爐,細細回想父親與他的點點滴滴,幾乎後面都是一片空白。人病了,人走了,恨也恨不起來。
休養三個月後,阿幸又重新回到忙碌的職場,只是他會斟酌身體情況。有時他會盯着手機,懷念一通令人煩躁的電話。
令 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