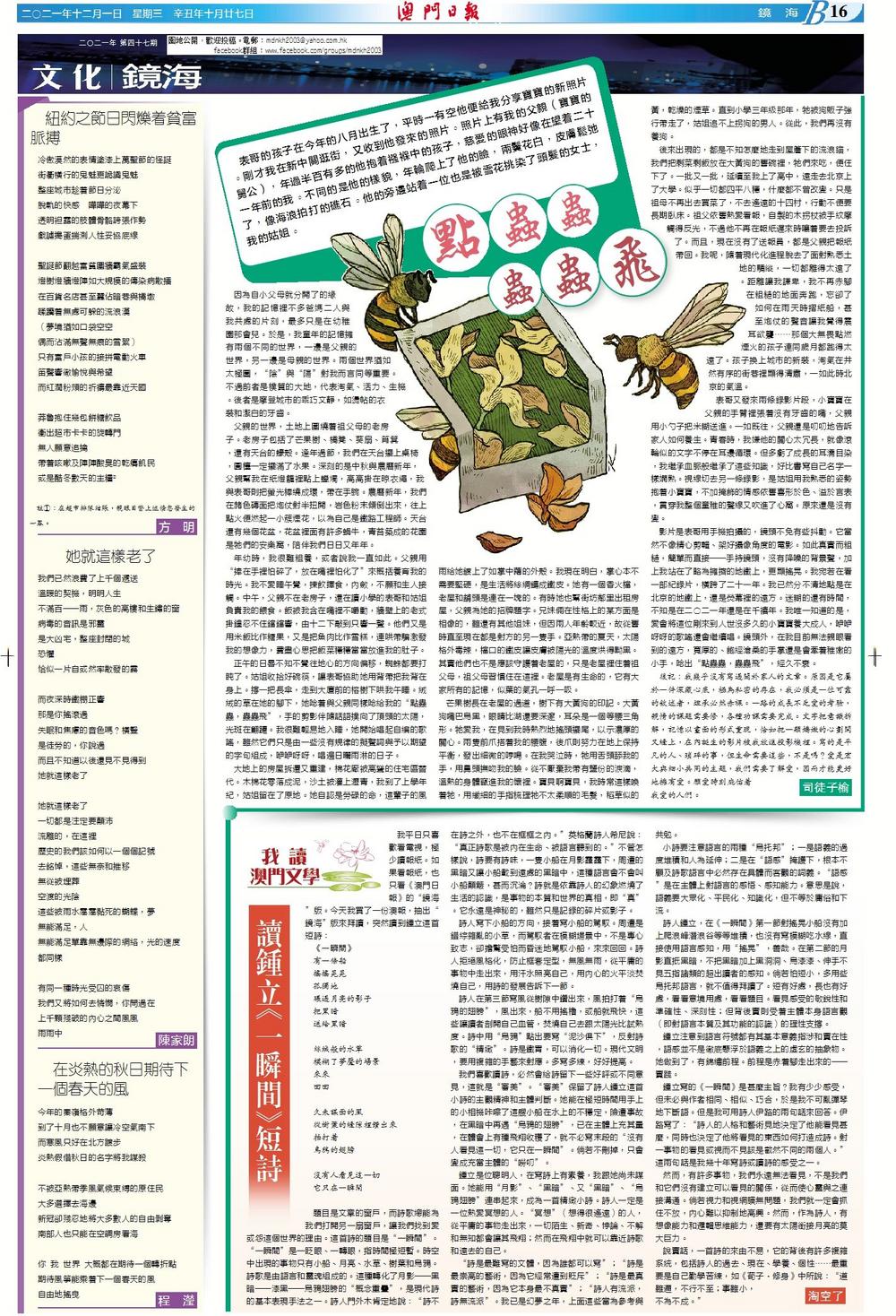點蟲蟲蟲蟲飛
表哥的孩子在今年的八月出生了,平時一有空他便給我分享寶寶的新照片。剛才我在新中關逛街,又收到他發來的照片。照片上有我的父親(寶寶的舅公),年過半百有多的他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慈愛的眼神好像在望着二十一年前的我。不同的是他的樣貌,年輪爬上了他的臉,兩鬢花白,皮膚鬆弛了,像海浪拍打的礁石。他的旁邊站着一位也是被雪花挑染了頭髮的女士,我的姑姐。
因為自小父母就分開了的緣故,我的記憶裡不多爸媽二人與我共處的片刻,最多只是在幼稚園那會兒。於是,我童年的記憶擁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邊是父親的世界,另一邊是母親的世界。兩個世界猶如太極圖,“陰”與“陽”對我而言同等重要。不過前者是樸質的大地,代表淘氣、活力、生機。後者是摩登城市的乖巧文靜,如燙帖的衣裝和潔白的牙齒。
父親的世界,土地上圍繞着祖父母的老房子。老房子包括了芒果樹、橋凳、葵扇、筲箕,還有天台的蠔殼。逢年過節,我們在天台擺上桌椅,圓檯一定擺滿了水果。深刻的是中秋與農曆新年,父親幫我在紙燈籠裡點上蠟燭,高高掛在晾衣繩,我與表哥則把螢光棒繞成環,帶在手腕。農曆新年,我們在赭色磚面把炮仗對半扭開,岩色粉末傾倒出來,往上點火便燃起一小簇煙花,以為自己是鐵路工程師。天台還有幾個花盆,花盆裡面有許多蝸牛,青苔築成的花園是牠們的安樂窩,陪伴我們日日又年年。
年幼時,我很難粗養,或者說我一直如此。父親用“捧在手裡怕碎了,放在嘴裡怕化了”來概括養育我的時光。我不愛睡午覺,揀飲擇食,內斂,不願和生人接觸。中午,父親不在老房子,還在讀小學的表哥和姑姐負責我的餵食。飯被我含在嘴裡不嚼動,牆壁上的老式掛鐘忍不住鐺鐺響,由十二下敲到只響一聲。他們又是用米飯比作糖果,又是把魚肉比作雪糕,連哄帶騙激發我的想像力,費盡心思把飯菜穩穩當當放進我的肚子。
正午的日晷不知不覺往地心的方向偏移,蜘蛛都要打盹了。姑姐收拾好碗筷,讓表哥協助她用背帶把我背在身上。撐一把長傘,走到大廈前的榕樹下哄我午睡。絨絨的草在她的腳下,她唸着與父親同樣唸給我的“點蟲蟲,蟲蟲飛”,手的剪影伴隨話語撲向了頂頭的太陽,光斑在翩躚。我很難輕易地入睡,她開始唱起自編的歌謠,雖然它們只是由一些沒有規律的擬聲詞與予以期望的字句組成,咿咿呀呀,唱遍日曬雨淋的日子。
大地上的房屋拆遷又重建,棉花廠被高聳的住宅區替代。木棉花零落成泥,沙土被灌上瀝青,我到了上學年紀,姑姐留在了原地。她自認是勞碌的命,這輩子的風雨給她鍍上了如掌中繭的外殼。我現在明白,掌心本不需要堅硬,是生活將絲綢鑄成鐵皮。她有一個香火檔,老屋和舖頭是連在一塊的。有時她也幫街坊鄰里出租房屋,父親為她的招牌題字。兄妹倆在性格上的某方面是相像的,雖還有其他姐妹,但因兩人年齡較近,故從舊時直至現在都是對方的另一隻手。亞熱帶的夏天,太陽格外毒辣,檔口的鐵皮讓皮膚被陽光的溫度烘得黝黑。其實他們也不是應該守護着老屋的,只是老屋裡住着祖父母,祖父母習慣住在這裡。老屋是有生命的,它有大家所有的記憶,似葉的氣孔一呼一吸。
芒果樹長在老屋的過道,樹下有大黃狗的印記。大黃狗嘴巴烏黑,眼睛比湖還要深邃,耳朵是一個等腰三角形。牠愛我,在見到我時熱烈地搖頭擺尾,以示濃厚的關心。兩隻前爪搭着我的腰腹,後爪則努力在地上保持平衡,發出細微的哼鳴。在我哭泣時,牠用舌頭舔我的手,用鼻頭撫吻我的臉。從不厭棄我帶有鹽份的淚滴,溫熱的身體竄進我的懷裡。寶貝啊寶貝,我時常這樣喚着牠,用纖細的手指梳理牠不太柔順的毛髮,稻草似的黃,乾燥的煙草。直到小學三年級那年,牠被狗販子強行帶走了,姑姐追不上拐狗的男人。從此,我們再沒有養狗。
後來出現的,都是不知怎麼地走到屋簷下的流浪貓,我們把剩菜剩飯放在大黃狗的舊碗裡,牠們來吃,便住下了。一批又一批,延續至我上了高中,遠走去北京上了大學。似乎一切都四平八穩,什麼都不曾改變。只是祖母不再出去買菜了,不去遙遠的十四村,行動不便要長期臥床。祖父依舊熱愛看報,自製的木拐杖被手紋摩觸得反光,不過他不再在報紙遲來時嚷着要去投訴了。而且,現在沒有了送報員,都是父親把報紙帶回。我呢,隨着現代化進程脫去了面對熟悉土地的驕縱,一切都離得太遠了。距離讓我謙卑,我不再赤腳在粗糙的地面奔跑,忘卻了如何在雨天時摺紙船,甚至炮仗的聲音讓我覺得震耳欲聾……那個大無畏點燃煙火的孩子連同歲月都跑得太遠了。孩子換上城市的新裝,淘氣在井然有序的街巷裡顯得清肅,一如此時北京的氣溫。
表哥又發來兩條錄影片段,小寶寶在父親的手臂裡張着沒有牙齒的嘴,父親用小勺子把米糊送進。一如既往,父親還是叨叨地告訴家人如何養生。青春時,我嫌他的關心太冗長,就像滾輪似的文字不停在耳邊循環。但多虧了成長的耳濡目染,我繼承血脈般繼承了這些知識,好比書寫自己名字一樣嫻熟。視線切去另一條錄影,是姑姐用我熟悉的姿勢抱着小寶寶,不加掩飾的情感依舊喜形於色、溢於言表,貫穿我整個童稚的聲線又吹進了心窩。原來還是沒有變。
影片是表哥用手機拍攝的,鏡頭不免有些抖動。它當然不像精心剪輯、架好攝像角度的電影。如此真實而粗糙,簡單而直接——手持鏡頭,沒有降噪的背景聲,加上我站在了略為擁擠的地鐵上,更顯搖晃。我宛若在看一部紀錄片,橫跨了二十一年。我已然分不清地點是在北京的地鐵上,還是熒幕裡的遠方。迷糊的還有時間,不知是在二〇二一年還是在千禧年。我唯一知道的是,愛會將這位剛來到人世沒多久的小寶寶養大成人,咿咿呀呀的歌謠還會繼續唱。鏡頭外,在我目前無法親眼看到的遠方,寬厚的、飽經滄桑的手掌還是會牽着稚嫩的小手,唸出“點蟲蟲,蟲蟲飛”,經久不衰。
後記:我幾乎沒有寫過關於家人的文章。原因是它屬於一件深藏心底,極為私密的存在,我必須是一位可靠的敘述者,坦承必然赤裸。一路的成長不乏愛的考驗,親情的課題需要修,各種功課需要完成。文字把意識拆解,記憶以畫面的形式重現,恰如把一顆嬌嫩的心劃開又縫上,在內誕生的影片被我放進投影機裡。寫的是平凡的人、瑣碎的事,但生命需要這些,不是嗎?愛是宏大與細小共同的主題,我們需要了解愛,因而才能更好地擁有愛。願愛時刻庇佑着我愛的人們。
司徒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