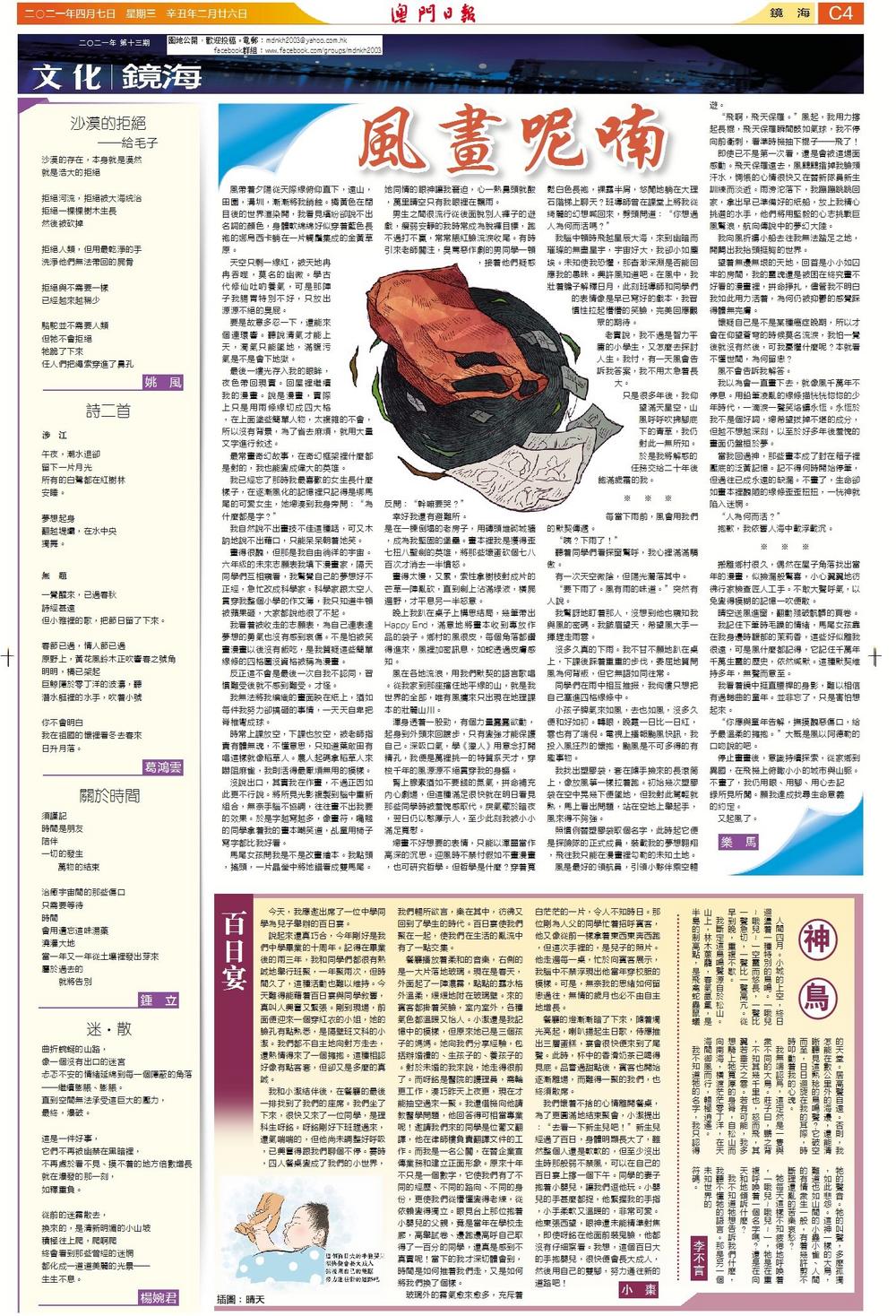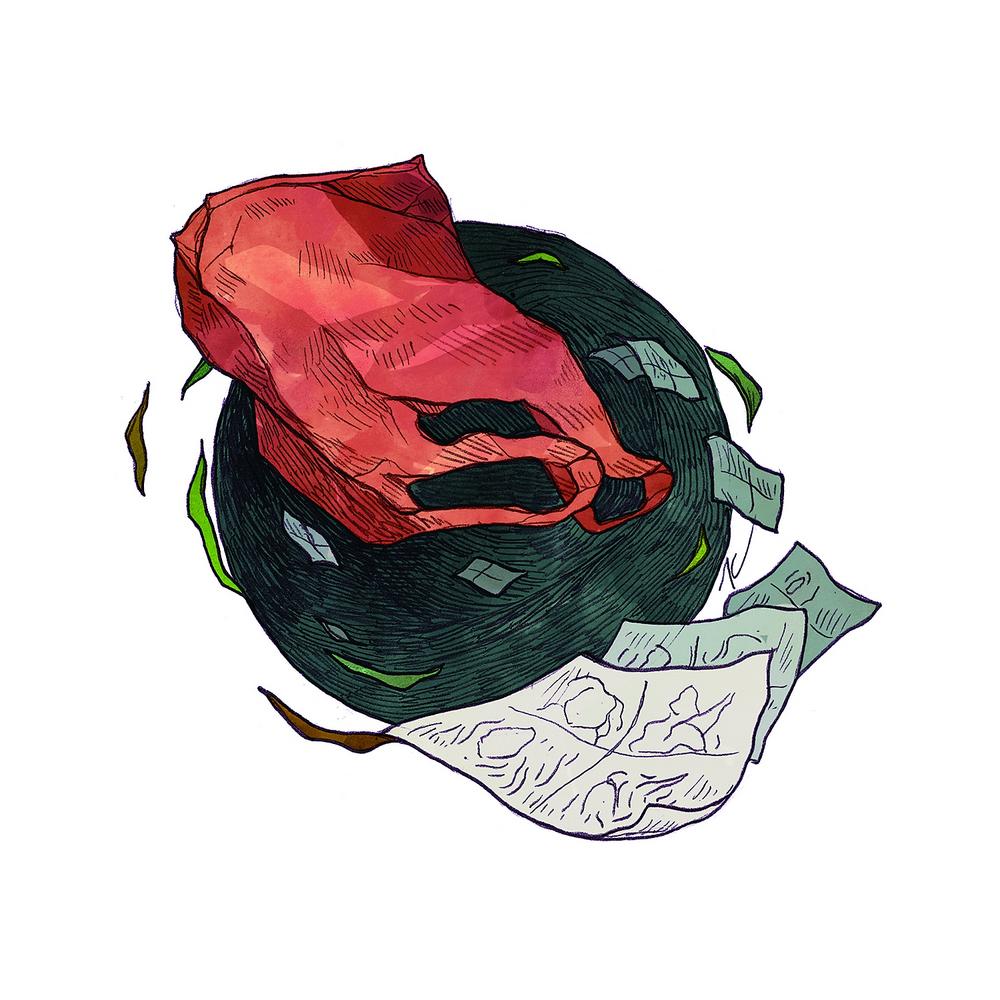風畫呢喃
風帶着夕陽從天際線俯仰直下,遠山,田園,溝圳,漸漸將我銷蝕。橘黃色在閉目後的世界渲染開,我看見繽紛卻說不出名詞的顏色,身體軟綿綿好似穿着藍色長袍的娜烏西卡躺在一片觸鬚集成的金黃草原。
天空只剩一線紅,被天地冉冉吞噬,莫名的幽微。學古代修仙吐吶養氣,可是那陣子我腸胃特別不好,只放出源源不絕的臭屁。
要是故意多忍一下,還能來個連環響。聽說清氣才能上天,濁氣只能墜地,滿腹污氣是不是會下地獄。
最後一縷光存入我的眼眸,夜色帶回現實。回屋裡繼續我的漫畫。說是漫畫,實際上只是用兩條線切成四大格,在上面塗些簡單人物,太複雜的不會,所以沒有背景,為了省去麻煩,就用大量文字進行敘述。
最常畫奇幻故事,在奇幻框架裡什麼都是對的,我也能變成偉大的英雄。
我已經忘了那時我最喜歡的女生長什麼樣子,在逐漸風化的記憶裡只記得是綁馬尾的可愛女生,她總湊到我身旁問:“為什麼都是字?”
我自然說不出畫技不佳這種話,可又木訥地說不出藉口,只能呆呆朝着她笑。
畫得很醜,但那是我自由徜徉的宇宙。六年級的未來志願表我填下漫畫家,隔天同學們互相窺看,我驚覺自己的夢想好不正經,急忙改成科學家。科學家跟太空人貫穿我整個小學的作文簿,我只知道牛頓被蘋果砸,大家都說他很了不起。
我看着被收走的志願表,為自己連表達夢想的勇氣也沒有感到哀傷。不是怕被笑畫漫畫以後沒有飯吃,是我質疑這些簡單線條的四格圖沒資格被稱為漫畫。
反正這不會是最後一次自我不認同,習慣難受後就不感到難受。才怪。
我無法將我編織的畫面映在紙上,猶如每件我努力卻搞砸的事情,一天天自卑把脊椎彎成球。
時常上課放空,下課也放空,被老師指責有體無魂,不懂意思,只知道葉啟田有唱這樣就像稻草人。農人起碼拿稻草人來嚇阻麻雀,我則活得最厭煩無用的模樣。
沒說出口,其實我在作畫,不過正因如此更不行說。將所見光影複製到腦中重新組合,無奈手腦不協調,往往畫不出我要的效果。於是字越寫越多,像畫符,嘴賤的同學拿着我的畫本嘲笑道,乩童用椅子寫字都比我好看。
馬尾女孩問我是不是改畫繪本。我點頭,搖頭,一片晶瑩中將她錯看成雙馬尾。她同情的眼神讓我窘迫,心一熱鼻頭就酸,萬里晴空只有我眼裡在飄雨。
男生之間很流行從後面脫別人褲子的遊戲,瘦弱安靜的我時常成為脫褲目標,跑不過打不贏,常常脹紅臉流淚收尾。有時引來老師關注,臭罵惡作劇的男同學一頓,接着他們疑惑反問:“幹嘛要哭?”
幸好我還有避難所。是在一棟倒塌的老房子,用磚頭堆砌城牆,成為我堅固的堡壘。畫本裡我是獲得歪七扭八聖劍的英雄,將那些壞蛋砍個七八百次才消去一半憤怒。
畫得太慢,又累,索性拿樹枝對成片的芒草一陣亂砍,直到劍上沾滿綠液,橫屍遍野,才平息另一半怒意。
晚上我趴在桌子上構思結局,幾筆帶出Happy End,滿意地將畫本收到專放作品的袋子。鄉村的風很皮,每個角落都鑽得進來,風裡加密訊息,如蛇透過皮膚感知。
風在各地流浪,用我們默契的語言歌唱。從我家到那座擋住地平線的山,就是我世界的全部,唯有風攜來只出現在地理課本的壯麗山川。
渾身透着一股勁,有個力量蠢蠢欲動,起身到外頭來回踱步,只有變強才能保護自己。深吸口氣,學《獵人》用意念打開精孔,我便是萬裡挑一的特質系天才,穿梭千年的風源源不絕貫穿我的身軀。
腎上腺素猶如不要錢的氮氣,拼命補充內心劇場,但這種滿足很快就在明日看見那些同學時被羞愧感取代。戾氣藏於暗夜,翌日仍以憨厚示人,至少此刻我被小小滿足寬慰。
總畫不好想要的表情,只能以渾噩當作高深的沉思。迎風時不禁忖假如不畫漫畫,也可研究哲學。但哲學是什麼?穿着寬鬆白色長袍,裸露半肩,悠閒地躺在大理石階梯上聊天?班導師曾在課堂上將我從綺麗的幻想喊回來,劈頭問道:“你想過人為何而活嗎?”
我腦中頓時飛越星辰大海,來到幽暗而璀璨的無盡星宇,宇宙好大,我卻小如塵埃。未知使我恐懼,那杳渺深淵是否能回應我的愚昧。興許風知道吧。在風中,我壯着膽子解釋日月,此刻班導師和同學們的表情像是早已寫好的戲本,我習慣性拉起懵懵的笑臉,完美回應觀眾的期待。
老實說,我不過是智力平庸的小學生,又怎麼去探討人生。我忖,有一天風會告訴我答案,我不用太急着長大。
只是很多年後,我仰望滿天星空,山風呼呼吹拂腳底下的青草,我仍對此一無所知。於是我將解惑的任務交給二十年後飽滿歲霜的我。
※ ※ ※
每當下雨前,風會用我們的默契傳遞。
“咦?下雨了!”
聽着同學們看探窗驚呼,我心裡滿滿驕傲。
有一次天空微陰,但陽光灑落其中。
“要下雨了。風有雨的味道。”突然有人說。
我驚訝地盯着那人,沒想到他也窺知我與風的密碼。我皺眉望天,希望風大手一揮趕走雨雲。
沒多久真的下雨。我不甘不願地趴在桌上,下課後踩着重重的步伐,委屈地質問風為何背叛,但它無語如同往常。
同學們在雨中相互推掇,我佝僂只想把自己塞進四格線條中。
小孩子脾氣來如風,去也如風,沒多久便和好如初。轉眼,晚霞一日比一日紅,雲也有了端倪。電視上播報颱風快訊,我投入風狂烈的懷抱,颱風是不可多得的有趣事物。
我找出塑膠袋,套在隨手撿來的長滾筒上,像放風箏一樣拉着跑。初始幾次塑膠袋在空中晃幾下便墜地,但我對此駕輕就熟,馬上看出問題,站在空地上舉起手,風來得不夠強。
照慣例替塑膠袋取個名字,此時起它便是探險隊的正式成員,裝載我的夢想翱翔,飛往我只能在漫畫裡勾勒的未知土地。
風是最好的領航員,引領小夥伴乘空暢遊。
“飛啊,飛天保羅。”風起,我用力撐起長棍,飛天保羅瞬間鼓如氣球,我不停向前衝刺,看準時機抽下棍子——飛了!
即使已不是第一次看,還是會被這場面感動。飛天保羅遠去,風颼颼揩掉我臉頰汗水,惆悵的心情很快又在替新隊員新生訓練而淡逝。雨滂沱落下,我蹦蹦跳跳回家,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紙船,放上我精心挑選的水手,他們將用堅毅的心志挑戰巨風驚浪,航向傳說中的夢幻大陸。
我向風祈禱小船去往我無法踏足之地,開闢出我抬頭挺胸的世界。
望着無邊無垠的天地,回首是小小如囚牢的房間,我的靈魂還是被困在終究畫不好看的漫畫裡,拼命掙扎,儘管我不明白我如此用力活着,為何仍被抑鬱的感覺踩得體無完膚。
懷疑自己是不是某種癌症晚期,所以才會在仰望蒼穹的時候莫名流淚,我怕一覺後就沒有然後,可我憂懼什麼呢?本就看不懂世間,為何留戀?
風不會告訴我解答。
我以為會一直畫下去,就像風千萬年不停息。用鉛筆凌亂的線條描恍恍惚惚的少年時代,一滴淚一聲笑烙鑄永恆。永恆於我不是個好詞,總希望拔掉不堪的成分,但越不想越深刻,以至於好多年後羞愧的畫面仍盤桓於夢。
當我回過神,那些畫本成了封在箱子裡壓底的泛黃記憶。記不得何時開始停筆,但過往已成永遠的缺漏。不畫了,生命卻如畫本裡醜陋的線條歪歪扭扭,一恍神就陷入迷惘。
“人為何而活?”
抱歉,我依舊人海中載浮載沉。
※ ※ ※
搬離鄉村很久,偶然在屋子角落找出當年的漫畫,似撿漏般驚喜,小心翼翼地彷彿行家檢查匠人工手。不敢大聲呼氣,以免變得模糊的記憶一吹便散。
晴空送風進窗,翻動殘破骯髒的頁卷。
我記住下筆時毛躁的情緒,馬尾女孩靠在我身邊時馥郁的茉莉香,這些好似離我很遠,可是風什麼都記得,它記住千萬年千萬生靈的歷史,依然緘默。這種默契維持多年,無聲而意至。
我看着鏡中挺直腰桿的身影,難以相信有過蜷曲的童年。並非忘了,只是害怕想起來。
“你應與童年告解,撫摸醜惡傷口,給予最溫柔的擁抱。”大概是風以阿德勒的口吻說的吧。
停止畫畫後,意識持續探索,從家鄉到異國,在飛機上俯瞰小小的城市與山脈。不畫了,我仍用眼、用腳、用心去記錄所見所聞。願我達成找尋生命意義的約定。
又起風了。
樂 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