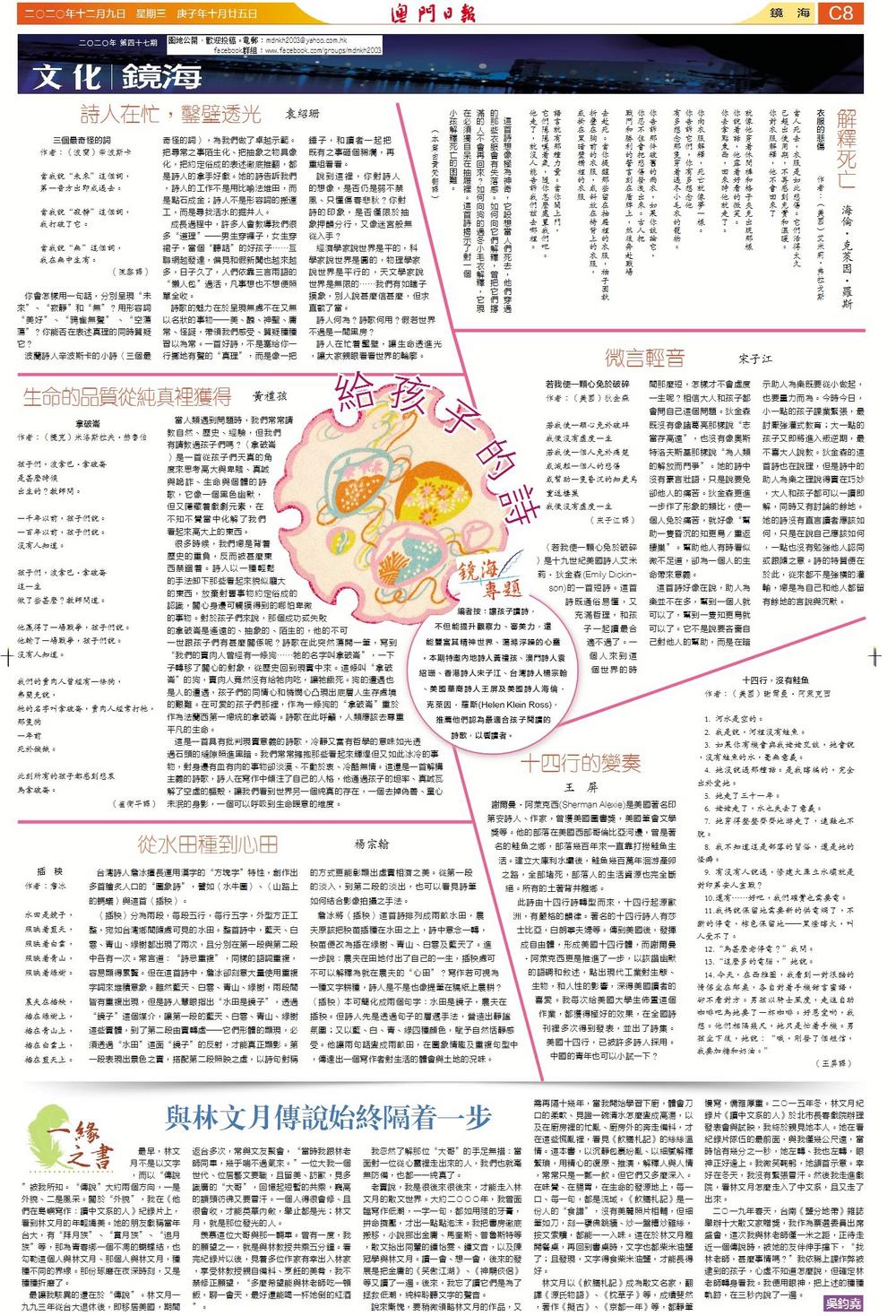與林文月傳說始終隔着一步
最早,林文月不是以文字,而以“傳說”被我所知。“傳說”大約兩個方向,一是外貌、二是風采。關於“外貌”,我在《他們在島嶼寫作:讀中文系的人》紀錄片上,看到林文月的年輕嬌美。她的朋友戲稱當年台大,有“拜月族”、“賞月族”、“追月族”等,那為青春綁一個不凋的蝴蝶結,也勾勒這個人與林文月、那個人與林文月,種種不同的界線。那份琢磨在夜深時刻,又是種種折磨了。
最讓我駭異的還在於“傳說”。林文月一九九三年從台大退休後,即移居美國,期間返台多次,常與文友聚會,“當時我跟林老師同車,幾乎喘不過氣來。”一位大我一個世代、位居藝文要職,且留美、訪歐,見多識廣的“大哥”,回憶起短暫的共乘,巍高的額頭彷彿又要冒汗。一個人得很會修、且很會收,才能英華內斂,舉止都是光;林文月,就是那位發光的人。
羨慕這位大哥與那一輛車。曾有一度,我的願望之一,就是與林教授共乘五分鐘。看完紀錄片以後,見着多位作家有幸出入林家,享受林教授親自備料、烹飪的美肴,我不禁修正願望,“多麼希望能與林老師吃一頓飯,聊一會天,最好還能喝一杯她倒的紅酒”。
我忽然了解那位“大哥”的手足無措:當面對一位從心靈裡走出來的人,我們也就毫無防備,也都一一純真了。
老實說,我是很後來很後來,才能走入林文月的散文世界。大約二○○○年,我曾面臨寫作低潮,一字一句,都如用殘的牙膏,拼命擠壓,才出一點點泡沫。我把書房徹底搬移,小說挪出金庸、馬奎斯、普魯斯特等,散文抬出同輩的鍾怡雯、鍾文音,以及陳冠學與林文月。讀一會、想一會,後來的發展是把金庸的《笑傲江湖》、《神鵰俠侶》等又讀了一遍。後來,我忘了讀它們是為了拯救低潮,純粹聆聽文字的聲音。
說來慚愧,要稍微領略林文月的作品,又需再隔十幾年,當我開始學習下廚,體會刀口的柔軟、見證一碗清水怎麼變成高湯,以及在廚房裡的忙亂、廚房外的奔走備料,才在這些慌亂裡,看見《飲膳札記》的絲絲溫情。這本書,以沉靜包裹紛亂、以細膩解釋繁瑣,用精心的復原、推演,解釋人與人情,常常只是一瓢一飲。但它們又多麼深入。在味覺、在腸胃,在生命的發源地上,每一口、每一句,都是流域。《飲膳札記》是一份人的“食譜”,沒有美麗照片相輔,但細筆如刀,刻一甕佛跳牆、炒一盤糟炒雞絲,按文索驥,都能一一入味。這在於林文月離開餐桌,再回到書桌時,文字也都柴米油鹽了;且發現,文字得食柴米油鹽,才能長得好。
林文月以《飲膳札記》成為散文名家,翻譯《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成績斐然,著作《擬古》、《京都一年》等,都靜筆慢寫,儒雅厚重。二○一五年冬,林文月紀錄片《讀中文系的人》於北市長春戲院辦理發表會與試映,我終於親見她本人。她在看紀錄片隊伍的最前面,與我僅幾公尺遠,當時恰有幾分之一秒,她左轉、我也左轉,眼神正好逢上。我微笑鞠躬,她頷首示意。幸好在冬天,我沒有緊張冒汗。然後我走進戲院,看林文月怎麼走入了中文系,且又走了出來。
二○一九年春天,台南《鹽分地帶》雜誌舉辦十大散文家贈獎,我作為票選委員出席盛會,這次我與林老師僅一米之距,正待走近一個傳說時,被她的友伴伸手擋下,“找林老師,甚麼事情嗎?”我依稀上課作弊被逮到的孩子,心虛不知道怎麼說,但確定林老師轉身看我。我便用眼神,把上述的種種軌跡,在三秒內說了一遍。
吳鈞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