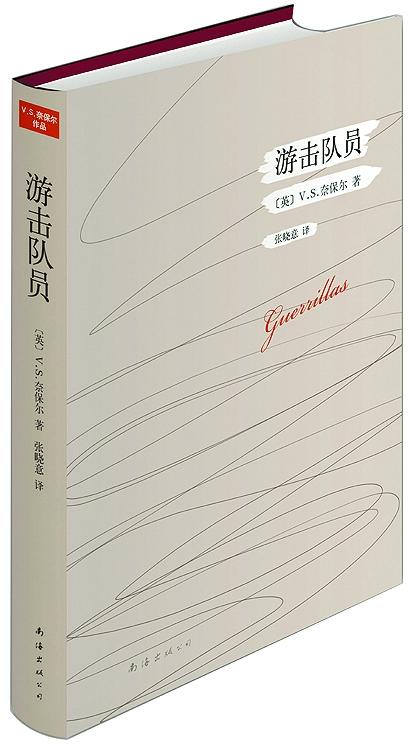後殖民時代的小戰役
奈保爾在《游擊隊員》裡,有一個遊戲叫“你是怎麼度過你的二十四小時的?”他在小說中安排的幾個主要人物都玩了這個言語幻想類遊戲,他們紛紛回想與列舉。但在最後,作者通過書中人物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我們描述的正是現在過的或者曾經過的生活。背景可能會變,但是沒有人會重新開始或者幹甚麼新的事情……我們就是我們自己,我們不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別人……沒有人會開始新的生活。”
奈保爾出生於中美洲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一個印度婆羅門家庭,一九五○年獲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一九五五年定居英國,並開始文學創作。奈保爾的個人身世使得他身上有着多種文化標籤。在印度人眼裡,他是英國人;在英國人眼裡,他是印度人,他就這樣被夾在身份認同的屏障裡。他的小說很多帶有自傳式成分,關注種族、殖民、多元文化的融合和衝突等內容,如他自己所言“我就是我作品的總和”。二○○一年奈保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天賦和才華而論,奈保爾當居在世作家之首”。這是《紐約時報》對當時八十五歲的大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毫不保留的讚譽。他與石黑一雄、拉什迪並稱“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在我讀過的作家中,奈保爾最善於從多角度的文明視野中觀察事物,他不僅如其所言能夠站遠幾步看到一個事物的各種面向,還能夠同時從不同價值世界的體系中,來比對同一事物在不同處境中的不同意義。他曾在《作家看人》中說:“我這一輩子,時時不得不考慮各種觀察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如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這種觀察不僅是作為書寫者的基本功,好比奈保爾從最初的《米格爾街》的“平面”觀察逐漸學習“退後一步、兩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場景”的更為複雜全面的觀察技巧,進而它還是一種對“自我”文化身份的探究方式。
他在《游擊隊員》中的這種對環境、文化氛圍的極具洞察力的描寫尤其尖銳透徹。誠然,環境描寫在小說中必不可少,但對於小說的節奏而言,讀者會恨不得立刻跳過去閱讀緊張的故事情節。很少會有像這類懸疑氣質的小說,能夠把描寫這部分與故事的氛圍融合得如此貼切又讓人着迷,那些文字讓你津津有味之餘,甚至想停下來感受當下的氛圍,再聽他繼續講故事。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行走過世界的作家,他一直在學習和訓練自己的“觀察方式,用細膩的筆觸揭開後殖民時代的種種傷疤——政治腐敗、部落紛爭、文化空缺。他曾遊歷過非洲大陸、南北美洲以及許多伊斯蘭國家,探尋後殖民時期的風土人情。《游擊隊員》便是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為背景,講述了加勒比海國家的人民尋求自由獨立的艱難,也描述了解放運動的局限性。小說塑造了加勒比海地區的多元文化所孕育的三個人物形象,他們血統複雜,有華人、黑人、白人和印度裔血統,都有一種莫名漂泊感和文化上的無根感。他們率領游擊隊和白人政府鬥爭,主人公最後遭到滅頂之災,革命的最終命運是徹底覆滅。
“當人人都想戰鬥,也就沒有甚麼值得去戰鬥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戰役,人人都是游擊隊員。”奈保爾寫出了一個後殖民時代的困境的夢碎和心滅。
花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