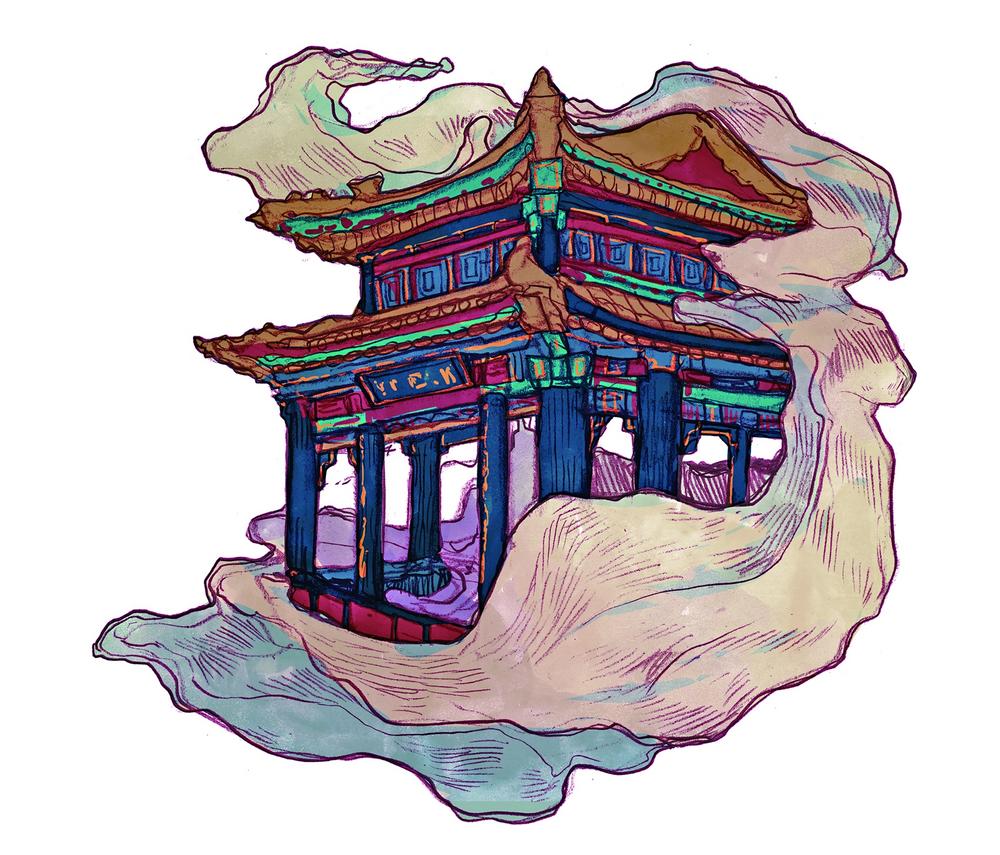遊漱芳齋
得益於瓊瑤女士的創作,北京故宮漱芳齋成了今人嚮往之所。
這所始建於明朝永樂十八年的小殿,是乾隆帝的至愛。年輕時闢為書齋,勤學苦練。登基後,每歲新正端坐齋中,開筆書福。逢年過節,還常常帶攜一群王公大臣,侍奉皇太后在漱芳齋進膳、看戲。
二○一八年春,我跟隨眾友從遊故宮,有緣一窺漱芳齋。北地三月依舊蕭索,幸遇一碧如洗的好天,友儕同行,言笑晏晏。曾有一段日子,漱芳齋對外開放,但後來很少接待訪客。齋外遊人如鯽、喧闐四起,齋内門可羅雀,冷清得十分突兀。這方小天地,倒是契合“漱芳”洗滌心性、美好德行的寓意。
迥異於巍峨宮殿,漱芳齋呈“工”字形佈局,別具一格、清新雅致,凸顯出文化面相,隱去了權力表徵。前殿東壁整面牆的多寶閣,擺放着當年乾隆精心挑選的珍寶古玩,巡睃其間瓷器居多,便輕喚癡迷此道的好友來賞。而房內疏疏落落點綴些文房小件,方才令我備感親切。後殿名為“金昭玉粹”,殿中放置一扇紫檀屏風,金粉漆上乾隆御筆,詩文寄寓儒家思想治國安邦的理想——“天人三策對,帝名相江都……政經真法訓,漢室最醇儒。詮義書屏扆,將為出治模。”
乾隆為人好風雅、興別致,從他苦心營造漱芳齋可見一斑。行進殿內風雅存小戲台,在仿竹木雕抱柱上懸掛的一幅楹聯,竟做成兩張古琴模樣,上書——自喜軒窗無俗韻,聊將山水寄清音。齋內處處氤氳着濃郁的文化氛圍,即便擺設稍顯刻意,可這份用心也讓人動容。
我來到一張圓桌前,停下腳步仔細打量,内圈雲石打磨光亮,石面隱現高山流水、遠天逸雲,外環木面刨得平滑似水,架身漆如明鏡。蹲低身子看底板,做工卻相當馬虎,木痕凹凸。一如我去圓明園時所見,正面與反面的光景全然不同,那些精美石刻的後面也是粗糙不平的。工匠們從五湖四海徵召而來,手藝高超精湛,可為皇帝服役,心中並不順氣。圓明園中倒塌的條石、方柱,可見的三面打磨得光可鑑人,而靠牆的那一面只草草修整,粗糲得過分誇張。彷彿惟有如此,工匠們的心氣方才平順些。他們握緊鑿子、揮動手錘,鏘、鏘、鏘,敲打身前頑石,石屑飛射、火星時濺,力圖將不堪的一面潛藏、心底的怨懟隱閉,遺給子孫去解讀,留給後代去感應。
步出齋房,徘徊園中,我靠在階前石柱,全身冷冽。這種感覺,同我首次到圓明園遺址時一樣強烈。那是多年前晚冬的某個黃昏,行經大水法,幾根殘柱卻還固執地矗立在斷垣殘壁間,支撐起一道門。夕陽穿落林間,打在身上,異常冷冽。
圓明園乃農業文明的巔峰之作。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作為征服者的滿人後裔,他們努力融入中華文明的主流,由此也開啓了所謂的“康乾盛世”。對於中華文明,乾隆孜孜汲汲一生,終得登堂入室,卻渾然不覺泰西之地醖釀着工業文明的巨變。
差不多同一時代的十八世紀,在蘇格蘭新拉納克,大衛 · 戴爾於一七八五年創立棉紡廠村莊,他利用克萊德河段湍急的瀑布、溪流為動力,帶動理查 · 阿克萊特發明的水力紡紗機,實行工廠化運作。大衛 · 戴爾的女婿、烏托邦理想主義者羅伯特 · 歐文接手經營新拉納克後,很快建成當世最大的工廠之一。設若將畫面切換到那時的英國社會,“鄉村建起了灰暗的廠房,城鎮竪起高聳的煙囪,工廠裏迴蕩着機器的轟響,高爐前噴發出鐵水的光亮。”在新拉納克高敞的車間中,一個個飛梭在英國紡織工人手中疾速滑動,而天朝讀書人仍舊緩步徘徊小書齋中,搖頭晃腦誦讀《四書五經》,農民依然面朝黃土背朝天,揮動鋤頭把緊犁鏵刨土耕田。碩大的蒸汽錘轟隆隆地鏘鳴,敲響了農業文明的喪鐘,工業巨力碾壓全球的號角響起,農業世界的征服者、被征服者都將遭受工業文明的巨大衝擊,煌煌中華此時已然落伍。
一七九二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出訪中國,謀求通商。七百多人的龐大使團,劈波斬浪大半年後抵達廣州,又因利益之爭、禮儀之辯擾攘數月,乾隆諭旨回應,“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此前,從《馬可波羅行記》風行的十四世紀到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時,出現數百年熱潮的“中國狂想”。歐洲不少思想巨擘仰慕東方,盛讚儒家文化與中國政治經驗。然而,馬戛爾尼訪華後,使團所見所聞大異於早先傳佈之情,他們的記錄和見聞完全顛覆了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馬戛爾尼這批歐洲人實實在在到過中國,見過中國皇帝的真正面目,感受到華夏大地的内在脈動,清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一語成讖。“先進的東方、落後的西方”,此時逆轉為“落後的東方、先進的西方”。
我們最初的切膚之痛當係船堅炮利,誠然現在看來那是膚淺的認知。英國經過十七世紀清教徒革命和光榮革命後,漢諾威王朝的權力日漸向下擴散,核心權力由國王掌中慢慢讓渡到貴族集團。議會開始掌權,政治制度開明,社會風氣漸化,貴族、紳士乃至尋常百姓都勇於奮進,整個社會迸發出强勁的創造力,且汲汲於財富追求,重商主義、自由貿易迭起,大不列顛島呈現出駸駸日上的氣象,終於催生了工業革命。平整的廠房取代尖聳的教堂,成為人類活動的軸心,農業文明率先蛻變,工業文明呱呱墜地。此刻的中國,雖處盛世年華,皇權無遠弗屆,卻已暮靄沉沉。此後的中國近代史篇章,一面是日薄西山、逐漸淪喪的沉淪史,一面是天啓英賢、革新中國的奮爭史。皇帝的宮殿,偌大的故宮,由中央權力的核心、農業文明的精萃,變身為博物院所,今人走馬觀花的勝景。
博物館中佈設的展櫃,恍若古物太平間。這些原本讓人把玩的物件,陳列其間,隔着玻璃罩供人遠觀。人眾絡繹不絕,仿如輪番參加憑弔,追悼儀式卻永不結束。一件三五百年前的巧作古物,靜靜存放博物館內,再過千年,他的生命、他的歷史也只不過三五百年。無人把賞,不被塵污,失卻主人的悲歡離合,遠離凡世的滄海橫流,在恆溫恆濕恆定的時空中,不再發生故事,他們的生命終結於此。為了所謂的永存,而放棄生命,甚至不許湮沒,博物館式不生不活、不死不滅的文物保育形態,值得今人深思。
在展櫃中被精心保存的傳統,與其沉睡不起、供人憑弔,不如被喚醒、被異化、被重塑。後人重新創造、再度詮釋的傳統,多少還葆有一絲生氣。與保留傳統相比,我們更需創造傳統。因為從一種文明形態的崩解,到另一種文明形態的重建,被創造的傳統乃是跨越文明溝壑的橋樑,乃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臍帶。只有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成功,孕育成為另一個獨立的文明體時,胎盤方可脫落,臍帶方可剪斷。農業文明的心臟——宮殿如是,工業文明的中樞——工廠如是。回想百多年來,中國風雲激蕩,不禁令人感慨。難道由於我們醒覺太遲、起步太緩,故而決心太厲、落手太重?文物無言,觀者無語,芳齋無聲。
新拉納克工廠持續經營近兩百年,直到一九六八年結業,如今名列世界文化遺產,每年吸引數以十萬計的遊客參觀。斑駁古舊的棉磨坊、長直周正的廠房、敞亮的工人社區、良善的配套設施,被蜿蜒的溪流舒展成一幅明媚的工業畫卷,帶映出羅伯特 · 歐文人文主義的餘暉。可這一切都正化作遺跡,農業文明也好、工業文明也罷,與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人們悄然邁入後現代,但後現代社會是什麽呢?回歸精神世界的求索嗎?誰也不知道。
我在漱芳齋前院盤桓、神思良久,那種冷冽的感覺漸漸消散。不大寬敞的天井中,建有一座高大戲台,牌匾寫着“昇平叶慶”。據傳,在宣統帝溥儀大婚期間,漱芳齋連演三天大戲,余叔岩、楊小樓等京劇名角出演。民國二十年,漱芳齋最後一次排戲,名旦尚小雲當時演了一齣《遊園驚夢》。那一刻,我的耳畔似乎響起鑼鼓經,“匡七台七匡七台七……”,恍惚聽見淒美的清音——夢迴鶯囀,亂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戲台樑柱間,幾隻雀鳥飛動,互傳檐語,嚶鳴呼晴。或者,這就是台口左右題寫“佾舞”“諧音”的原初意義吧。愣神之際,眾友早已齊聚前院,我們便踏過窄門,終究匯入了御花園的人潮。
胡 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