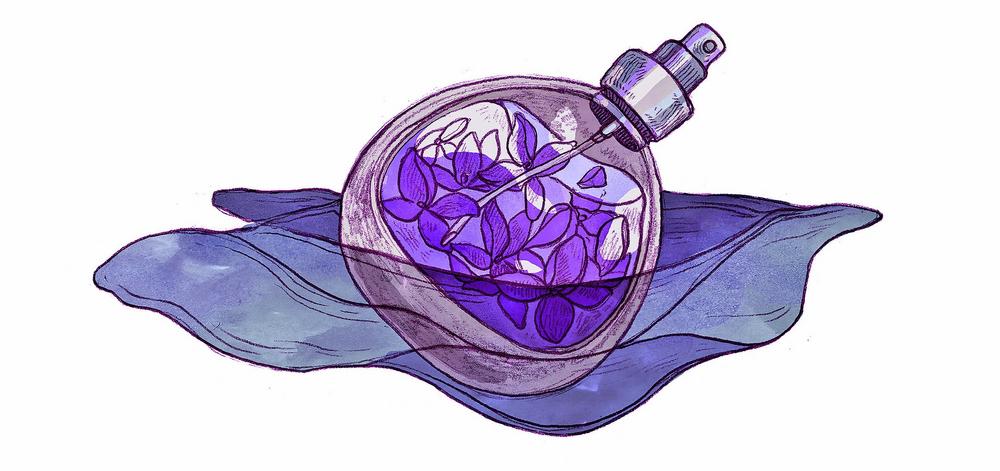四月的花束
黃竹熙讀中學的時候,每一次分別,他妹妹瘦小的肩膀上都背着一個很大的書包,默默地目送他。他假日去探親後,要在中港城搭船回澳。妹妹在香港跟着父親生活,慘無天日,後來他這樣覺得,但是前五年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她妹妹過着什麼樣的日子。
父母離婚的時候他才初一,妹妹讀小四,正是剛長高又還什麼都不太懂的年紀。離婚後他和妹妹分別跟了母親和父親。他爹很快又找了一個阿姨,有時候他會看見妹妹身邊的那個女人,不太漂亮,三十多歲,有點皺紋,但有自己獨特的韻味,對他爹很溫柔。
他能理解他爹喜歡這個女人勝於他媽的原因,他媽媽很強勢,他爹又花心,兩個人合不來,以前常吵架,分開後他媽經常出去見朋友和逛街,也會給他足夠的零花錢。去香港探望妹妹,他們吃飯時聊天,妹妹都是沉默的,她說後母真是個惡毒的女人,她會在早餐裡放藥品,上面有粉末,老爸都不知道。
他不太懂,包括那個溫柔阿姨為什麼會一直堅持不懈地往妹妹的食物、飲料裡放毒,為什麼會持續翻找妹妹的東西,剋扣她的零用錢。他聽到妹妹沒零用錢花,在香港這個物價高的地方,他每次都拿些錢給她。但他顯然沒看見妹妹瘦削又發黃的臉頰之下,那痛苦的靈魂,年紀輕的他是體會不了那樣的多愁善感和哀愁,妹妹曾經寫過幾句詩,“四月,鮮花倒在墓碑/鳥兒倒在密林,太陽永不升起/月兒停駐在我的背影裡”,他是過了很久,知道了那些已發生的種種事情,才知道這首詩的死亡氣息的濃烈。
妹妹死了,得病而死的。事發前一個月他才見過她,神情沒什麼異樣,妹妹在讀中學,正是拔高纖瘦的身材。吃飯時他還問了妹妹近況,讀書如何,她點了點頭,說一切都很好,還在努力想考入前十名。怎麼會這樣一夜之間死去,他用了很長時間去搞清真相,包括她的屍檢報告和醫院的病歷,還有她後母的反應。沒有任何收穫,沒有誰害死她,妹妹就是一直以來心臟都不好,所以臉色才差,有一天就自己在家這樣心臟病病發,死了。
死後經過了喪禮、入土,一切又恢復了常態。香港那邊父親有兩個後母的小孩,每天熱鬧,母親的生活仍然如此,上班、逛街、吃飯。妹妹死後,這個世界裡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只有他還記得他和他的妹妹,好像還停留在過去的迴圈內。
妹妹死了之後他從高三升讀大學。星期六的夜店吵鬧,昏藍和艷紅的顏色就像濃彩一樣染在他的白衫,他低下頭,銀色的耳釘就如一顆鑽石,亮在他的脖頸髮梢的尾端。DJ音樂如海浪一樣響徹耳邊,他撩起女生的長髮,對她說了些什麼。兩人對望,她可以看見黃竹熙纖長濃密的睫毛,幾乎把眼睛都蓋住,夜店的光線在他的鼻樑側留下一道筆直的紅光,像是玫瑰般鮮艷的紅。她太沉醉於這種混血美感的帥哥了,親切但又疏離,讓她這種遍閱男生無數的女孩,也差一點失控。
兩人在舞池親吻。這不是黃竹熙的第一次,在這之前還有很多次,自從他的身高達至一米八五,模樣足以和成年人相混之時。音樂切換的時候,他拿起一杯酒,藍色夏威夷,疲憊地倒在包廂的沙發上,搖動着酒杯內的冰塊。家輝剛跳完舞回來,竹熙對他笑了一下,家輝大吐苦水,“小A啊,頭先個車模又嬲了,話我成日去酺,讓她沒安全感,我先酺得兩次!”
“的確玩得癲,你有女朋友仲來這種地方?”黃竹熙說。
“你的觀念原來咁保守。”家輝瞪大了眼睛,搖搖頭,似乎不能相信他今天聽了些什麼。居然從他口中聽到說自己玩得“癲”,“哇,我們叫你黃竹熙是小A,不就因為你是夜店A級海王嗎?你明明咁多個女朋友!”
“都是夜店識的,逢場作戲,沒什麼女朋友。”黃竹熙閉着眼說。
“海王。”家輝搖搖頭,“太羨慕了,有你這種桃花運,不,只要把你啲女分一半我,我也不用被女朋友壓着蝦。”
“人地生得靚仔,你唔好發夢。”發哥拿着幾碟水果和炸雞,走了過來,“借下位。”
於是家輝和黃竹熙挪動了屁股,給發哥騰出兩個人的空位,才能放得入發哥。沒辦法,發哥年紀輕輕就一百七十斤,從中學開始就減不下去。他叉着炸雞,送到小A面前,“要不要食?”
竹熙張口食了,濃密的睫毛看着他的眼神很溫柔。
“Bro,唔好咁看我。”發哥受不了他的魅力,抱怨,“你有條女,你唔好再望着我笑。”
“啲混血感係唔同。”子鏵行了過來,於是三人又集體挪動屁股,給子鏵讓位。此時沙發已經被坐滿了,黃竹熙示意包廂的服務員,加多五支酒。
“點樣?同公衛條女,發展成點?”發哥問。
“唉,講起就心累,佢又拒絕我了。說起來已經分分合合兩次。”子鏵說。夜店局經常變成了吐苦水局,因為幾個人的感情狀態都很混亂,子鏵跟曉晴,屢次分合,放又放不下那個女生。家輝在談一個車模,但兩人因為性格不合,經常吵架。只有小A雲淡風輕,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竹熙說他以前中學的時候也有念念不忘的女孩,被分了兩次手就學會了喝酒,然後成了夜店海王。他自己也知道,不怪那個女孩,他未做好準備。因為妹妹去世,他沉默了幾年,那實在不是一個適合談戀愛的時候。他在錯的時候,還不成熟的年紀,遇到了對的人。只徒增遺憾。
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滋潤着紫丁香生長在死地。
他遇到了一個女孩,叫歐陽倩,在夜店認識的。她在斯坦福大學讀工商管理系,然後回國交換一年,順便找點兼職來做。她笑着說:“弟弟,你很靚仔,但並不是我會喜歡的類型。”
不是她喜歡的類型,意思就是可以跟你談,但不會跟你長久。她一年後就要回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這只是一場萍水相逢的戀愛。他知道的。她個性凜冽強勢,有着與生俱來、家境優越、富養的自信,儘管外貌五官稍顯平淡,但也無礙她由內而外,因腹有詩書而散發的氣質。他被她吸引了,也許是看見了她身上的完美和完整,填補了他內心缺失的某塊東西。
他迅速跟她在一起了,四月的某個下午,送了一束鮮紅色的玫瑰花。確定關係後,女孩盡了一切女友的義務,樣樣俱到,小A清楚這只是她一直以來的完美主義在作祟,談戀愛對她來說就像是完成老師的一份專題報告,只想盡善盡美,在老師那裡拿到一個A+而已。沒有多少感情的燃燒,每次黃竹熙和她親熱後,餘溫剛冷,動作剛停下半秒,女孩就推開他起身,說要去做事了。乾淨利落,毫不拖泥帶水,機械得如同應付任務的機器人。
歐陽倩跟母親打電話,簡單地補充了一下她最近和黃竹熙戀愛的近況。對面話筒傳來母親冰冷的聲音,“談戀愛不認真的話可以,跟這個靚仔玩下就好了,你很快要回美國繼承家族企業的。”
“知道了。”歐陽倩淡淡地應道,然後掛了電話。母親沒問過她任何的戀愛細節,最近生活的近況,只是提醒了她如何如何攻讀學位,學習MBA、金融經濟知識,繼承家族企業,這些年都是這樣,一樣的話語,不變的要求。她只是想喘一口氣,不是集團總裁的女兒,不是什麼活動在商圈的未來財務官、執行長。她只是一個有自己簡單的生活,談一場普通的,沒任何利益、家境條件交換的戀愛。
有時候小A真的能讓她鬆一口氣,他的安然自在,他天生的敏感和對人的情感之重視,對外在條件的輕視,像是微酸青芒果混合柑橘調的香水,撲面而來的清新和舒服感。這由不得她喜好做決定,她不能選她最愛的香水味道。
“喂,小A,這排瘦了啊!”家輝看黃竹熙來,拍了拍他的肩膀,說。
四個老友難得聚在一起,前一段時間約了好幾次都沒約成,發哥還是那個樣子,子鏵氣色好了點,看起來是又跟曉晴復合了。發哥遞了支酒給他,手又收回,“喔,忘記了,你這排戒酒。”
“嗯。明天還要去上堂,今晚不能喝那麼多酒。”竹熙笑道。發哥注意到,他連煙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戒了,最近見他都不再買煙。
“明天不是周六嗎?還上什麼堂。”子鏵不解。
“我報了個進修的課程,學程式語言的。”
“約錯了時間,應該約星期六晚的。”
“他星期天要去返工啊。”發哥笑着補充,“你以為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放假沒事做嗎?他現在夜晚都不見人了,宿舍不見他回來。”
“咦,在忙什麼?”
“去溫習啊。要到考試周了,還有好幾個報告要做。”
“哇,以前小A你同我地一齊墊底,而家拋下我們獨自努力了。”子鏵感歎搖頭。
“識了新女啊。”
“就係讀斯坦福,家裡很有錢那個?”
“對。”
“怪不得這排小A你過得咁辛苦啦,要努力賺錢配得上人地啊。”
“不會辛苦的。為了自己喜歡的人努力,感覺不了辛苦的。每日都很充實。”
“那她回斯坦福之後怎麼辦?”子鏵問。
“再挽留下吧,可能還有點機會呢。”黃竹熙苦笑着回答。
發哥感覺到他整個人精神面貌都變了,以前眉眼那一股風流和輕佻,不知不覺都收斂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穩重。他在無意識地靠近對方的生活圈子,談吐都變了樣。不知道小A怎麼做到的,可能這就是愛情的力量吧。
“我跟你說清楚了。”歐陽倩語調冷酷,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潮牌T恤,配一條黑色短裙,整個人看起來凌厲,“我不會跟你長久的,下一年六月一到我就回美國,我們老死不相往來。”
當她說出“老死不相往來”這句時,她小心翼翼觀察他的反應。小A有一米八五,就算低着頭也比她高一個頭。他深黑色濃密的睫毛,遮住了眼睛一大片,在眼窩上也投下了一片陰影。淺紅色的嘴唇,常帶給她一種易碎的感覺。她看不清楚小A的眼神,不過對方很淡定,這讓她鬆了一口氣。說出的氣話沒刺痛對方,回過味,那種勁上來了,她的心又隱隱抽痛着。
說起來,這也是她第一次拍拖。之前在美國讀書,學業繁忙,一直沒遇到適合的人。這次交換,其實也是回國放鬆下。不知道怎麼好好地進入一段感情,愛與被愛,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又氣憤自己老是在小A面前就表現得不體面了,就驚慌失措了,無意中刺痛了對方。
黃竹熙沒回答什麼。南灣湖的風拂過他的身畔,連風都為他停駐、黏緩,歐陽倩在想自己怎麼狠得下心傷害他的,這次真的撐不下去要分了吧。她還在胡思亂想之際,對方突然抱了上來。沉默的、高大的、黑色身影,好像山一樣,溫柔又動情。他側頭吻她的唇,先是輕柔擦過,然後再猛烈的攻勢。她心跳如擂鼓,腿一軟,差點倒在欄杆上。他一隻手扶住她的腰,有力、蒼勁如松柏。
她胡亂地應對,但自己也知道亂了分寸,才意識到她男朋友是那樣高大的人,是那樣有魅力的人。隨着時間的逝去,她對他的愛有增無減,不考慮其他外在條件和未來的愛,將她包圍,剛硬變得溫柔,滿身的刺變成了貓身上的軟毛。她閉着眼,把頭擱在小A胸膛上,“……其實,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
“我也是想努力看看的。”她快速地擦了擦眼淚,南灣湖的風將她眼眶中的潮濕吹散。
“嗯。”
“你真的不怪我?”
“不怪。”小A低頭說道。
暮春夏初,深紫色好像瀰漫了整片世界,花朵凋落的季節。他抽空去了妹妹的墳前。其實說是墳墓,只是一個小小的塔位。有妹妹的照片,生卒年份。塔位排列密集,上下方都有其他的逝者。連死後都那麼擁擠,無人在意。小A將鮮花放在她的塔位前,每次他在這個世界上,無助、空虛的時候,都會來找妹妹。她走後,他和這個世界的親密連接,斷失了很大一截。他跟父親、母親的關係都疏淡了,一年只聯繫幾次。他拿起電話,始終不知道該和他們聊些什麼,每次要聊起妹妹,想到那個已經永遠躺在白色之中閉眼的生命,又無話可說。
這次,他望着那張照片裡,永遠停留在十幾歲模樣的妹妹,內心的空虛不知不覺被填滿了。生命的喜悅翩然而至,雖然伴隨的是易碎與撕裂的痛楚,但至少好一點了。他想,因為有那個女孩的存在。
小A太疼他女朋友了。發哥他們覺得,好像寂寞了很久的人,久旱逢甘霖。每天接送女友放學,帶她去吃晚餐吃宵夜,研究可以做些什麼紅糖水減緩她經期的痛楚。一些出門時很小的細節,下雨時的傘面永遠偏向她多一點。
聚會時歐陽倩穿短裙,他會脫下自己的外套給女朋友遮上。她不喜歡小A往那種唱K喝酒的場合跑,於是小A也減少了去的頻率,連打扮都變得鄰家溫和了。雖然仍舊遮掩不了他的帥氣。
俯身於下午,我把我悲哀的網,灑向你那汪洋的眼睛。
歐陽倩向父母提出了想一年後回國工作的提議,被他們嚴詞否定,同時也否定了黃竹熙。他們難得用這樣嚴肅的態度,對她說,這樣的人不可能成為我的女婿,你斷了念頭,早點回美國吧。
她按捺着悲傷的心情告知他這件事。雖然她還是忍不住落淚了,並且抽泣得尤為厲害。他似乎早料到了這種結果,一切都化為徒勞的空虛感,蠶食着他的心臟。他抱住歐陽倩,“沒事,你已經努力了。我們都努力了。”
活着,上進,努力變得更優秀,愛人和被人所愛,得到完整的人脈關係。他用了很長的時間悼念妹妹,贖了自我欠下她那麼多年的罪。然而罪是贖不清的,轉而歐陽倩又欠了他的一樣。分開的時候是四月,再過十幾天就是他們交往的一周年了。五月是他們相遇的,殘忍的季節,她不忍心再度過五月了,她提了分手,那天她記得天地蒼白,微風不起,小A身上的香水是雪松、柏木淡淡的味道。他很少噴香水,那天突然就噴了。兩人像平時一樣擁抱了,她只記得了他身上的味道。然後轉身逃跑。
小A失蹤了。發哥說。
子鏵和家輝一開始還不相信,這樣一座小城市,那麼大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麼說失蹤就失蹤了。但兩天都聯絡不上他了。手機什麼的完全打不通,去了他家也沒有人。
他們到處尋找,後來最熟悉小A的發哥一拍腦袋,又不敢肯定自己的想法。他乘車來了南灣湖。
深夜了。熒熒燈火全部跌落在湖面上一樣,波光粼粼。小A抱着一束花,坐在湖邊,睡着了。
天光和湖色,將他融合得那樣渾然一體。就像睡在水裡一樣。
那束花是新買的。
以 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