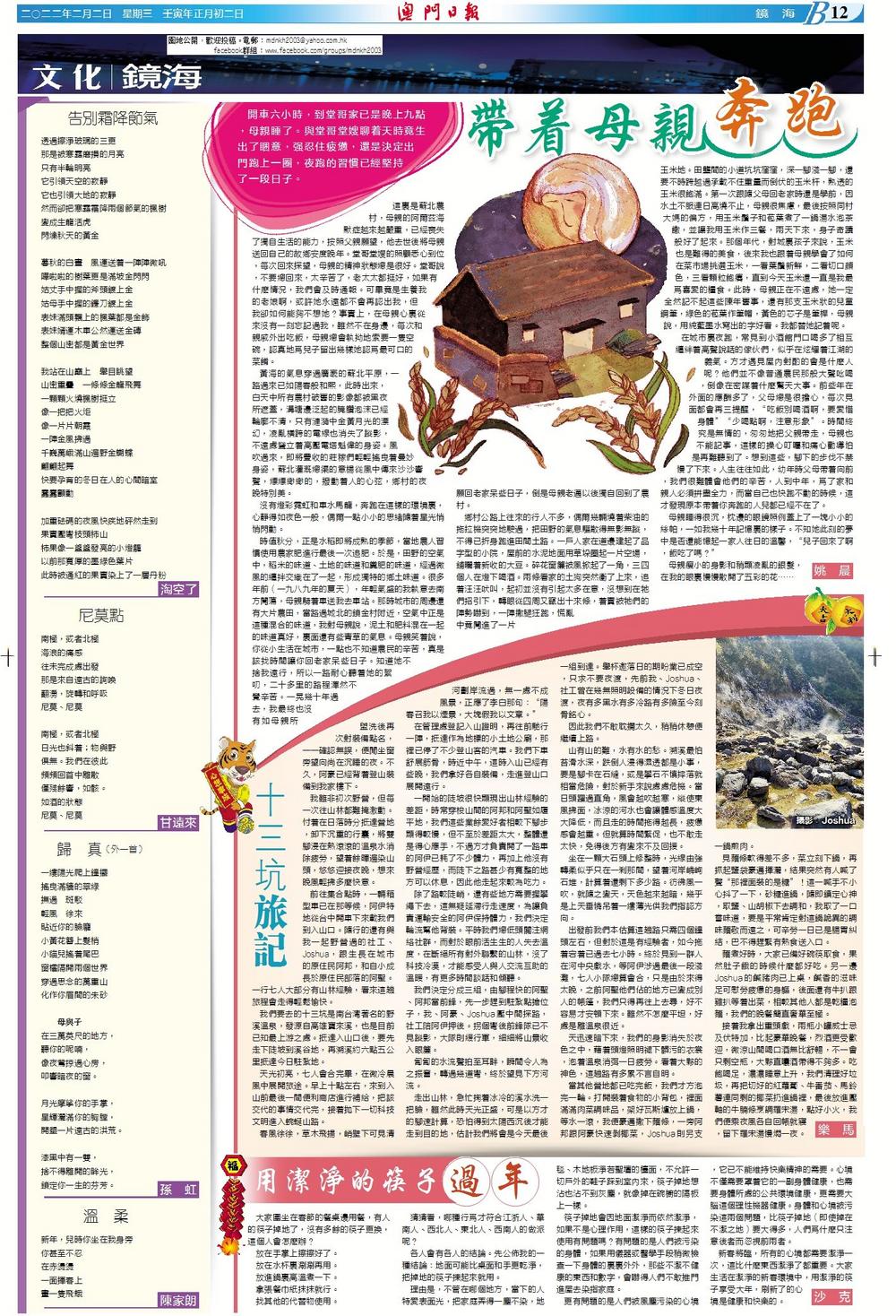帶着母親奔跑
開車六小時,到堂哥家已是晚上九點,母親睡了。與堂哥堂嫂聊着天時竟生出了睏意,强忍住疲憊,還是決定出
門跑上一圈,夜跑的習慣已經堅持
了一段日子。
這裏是蘇北農村,母親的阿爾茲海默症越來越嚴重,已經喪失了獨自生活的能力,按照父親願望,他去世後將母親送回自己的故鄉安度晚年。堂哥堂嫂的照顧悉心到位,每次回來探望,母親的精神狀態總是很好。堂哥說,不要總回來,太辛苦了,老太太都挺好,如果有什麽情況,我們會及時通報。可畢竟是生養我的老娘啊,或許她永遠都不會再認出我,但我卻如何能夠不想她?事實上,在母親心裏從來沒有一刻忘記過我,雖然不在身邊,每次和親戚外出吃飯,母親總會執拗地索要一隻空碗,認真地爲兒子留出幾樣她認爲最可口的菜餚。
黃海的氣息穿過廣袤的蘇北平原,一路過來已如陽春般和熙,此時出來,白天中所有農村破舊的影像都被黑夜所遮蓋,溝塘邊泛起的腌臢泡沫已經輪廓不清,只有漣漪中金黃月光的漂幻,凌亂橫跨的電線也消失了蹤影,不遠處聳立着高壓電塔魁偉的身姿。風吹過來,即將豐收的莊稼們輕輕搖曳着曼妙身姿,蘇北灌溉總渠的意楊從風中傳來沙沙響聲,縹縹緲緲的,撥動着人的心弦,鄉村的夜晚特別美。
沒有燈彩霓虹和車水馬龍,奔跑在這樣的環境裏,心靜得如夜色一般,偶爾一點小小的思緒隨着星光悄悄閃動。
時值秋分,正是水稻即將成熟的季節,當地農人習慣使用農家肥進行最後一次追肥。於是,田野的空氣中,稻米的味道、土地的味道和糞肥的味道,經過微風的纏拌交織在了一起,形成獨特的鄉土味道。很多年前(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年輕氣盛的我執意去南方闖蕩,母親騎着車送我去車站。那時城市的周邊還有大片農田,當路過城北的鎖金村附近,空氣中正是這種混合的味道,我對母親說,泥土和肥料混在一起的味道真好,裏面還有些青草的氣息。母親笑着說,你從小生活在城市,一點也不知道農民的辛苦,真是該找時間讓你回老家呆些日子。知道她不捨我遠行,所以一路耐心聽着她的絮叨,二十多里的路程渾然不覺辛苦。一晃幾十年過去,我最終也沒有如母親所願回老家呆些日子,倒是母親老邁以後獨自回到了農村。
鄉村公路上往來的行人不多,偶爾幾輛燒着柴油的拖拉機突突地駛過,把田野的氣息驅散得無影無蹤,不得已折身跑進田間土路。一戶人家在道邊建起了品字型的小院,屋前的水泥地面用草垛圈起一片空場,鋪曬着新收的大豆。碎花窗簾被風掀起了一角,三四個人在燈下喝酒。兩條看家的土狗突然衝了上來,追着汪汪吠叫,起初並沒有引起太多在意,沒想到在牠們招引下,轉眼從四周又竄出十來條,着實被牠們的陣勢嚇到,一陣撒腿狂跑,慌亂中竟闖進了一片玉米地。田壟間的小道坑坑窪窪,深一腳淺一腳,還要不時跨越過承載不住重量而倒伏的玉米杆,熟透的玉米很飽滿。第一次跟隨父母回老家時還是學前,因水土不服連日高燒不止,母親很焦慮,最後按照同村大媽的偏方,用玉米鬚子和苞葉煮了一鍋湯水泡茶饊,並讓我用玉米作三餐,兩天下來,身子奇蹟般好了起來。那個年代,對城裏孩子來說,玉米也是難得的美食,後來我也跟着母親學會了如何在菜市場挑選玉米,一看葉鬚新鮮,二看切口顔色,三看顆粒飽癟,直到今天玉米還一直是我最爲喜愛的糧食。此時,母親正在不遠處,她一定全然記不起這些陳年舊事,還有那支玉米狀的兒童鋼筆,綠色的苞葉作筆帽,黃色的芯子是筆桿,母親說,用純藍墨水寫出的字好看。我都替她記着呢。
在城市裏夜跑,常見到小酒館門口喝多了相互纏絆着高聲說話的傢伙們,似乎在炫耀着江湖的義氣。方才遇見屋內對酌的會是什麽人呢?他們並不像普通農民那般大聲吆喝,倒像在密謀着什麽驚天大事。前些年在外面的應酬多了,父母總是很擔心,每次見面都會再三提醒,“吃飯別喝酒啊,要愛惜身體”“少喝點啊,注意形象”。時間終究是無情的,匆匆地把父親帶走,母親也不能記事,這樣的操心叮囑和痛心勸導怕是再難聽到了。想到這些,腳下的步伐不禁慢了下來。人生往往如此,幼年時父母帶着向前,我們很難體會他們的辛苦,人到中年,爲了家和親人必須拼盡全力,而當自己也快跑不動的時候,這才發現原本帶着你奔跑的人兒都已經不在了。
母親睡得很沉,枕邊的眼鏡照例蓋上了一塊小小的絲帕,一如我幾十年記憶裏的樣子。不知她此刻的夢中是否還能憶起一家人往日的溫馨,“兒子回來了啊,飯吃了嗎?”
母親瘦小的身影和稍顯凌亂的銀髮,在我的眼裏慢慢散開了五彩的花……
姚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