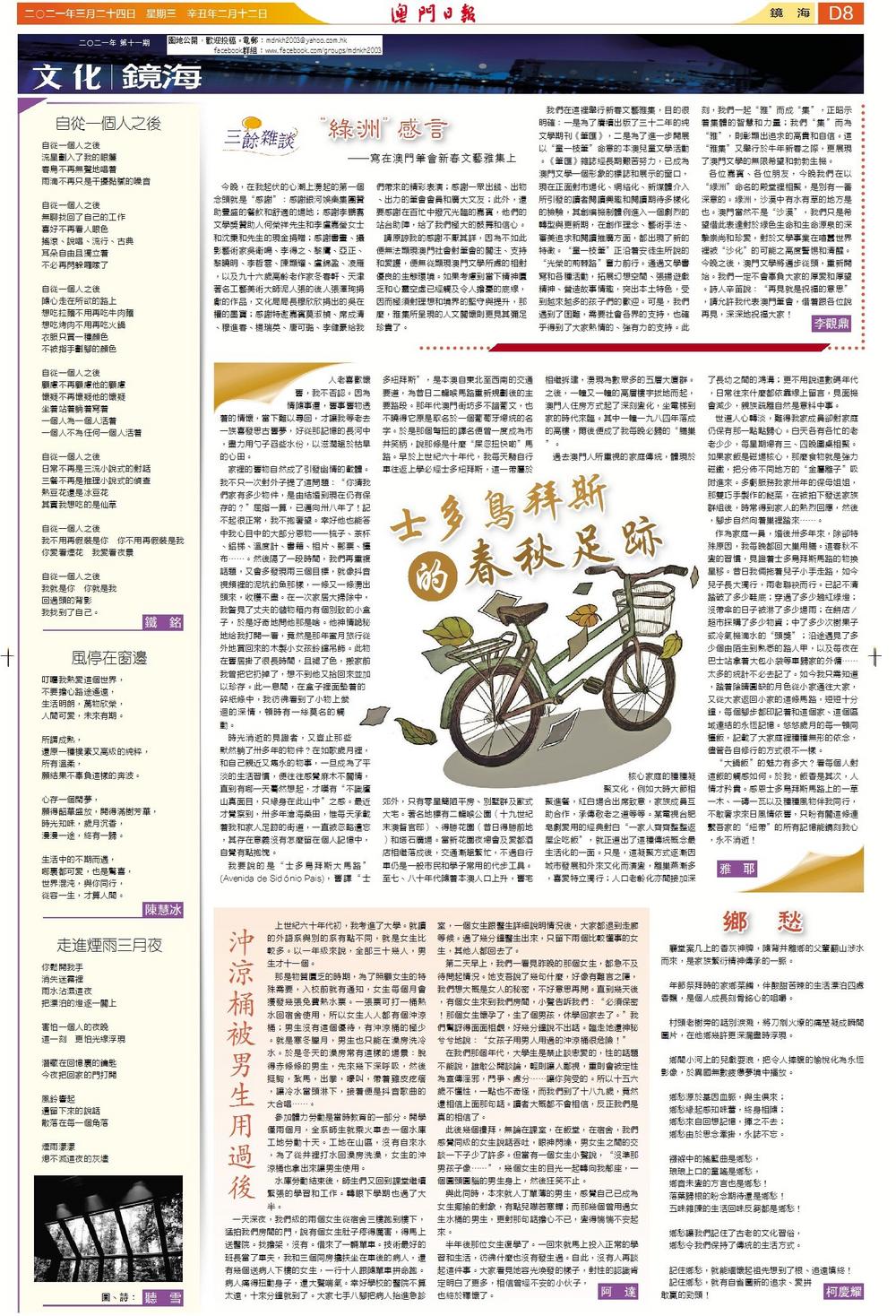士多鳥拜斯的春秋足跡
人老喜歡懷舊,我不否認。因為情隨事遷,舊事舊物透着的情懷,當下難以尋回,才讓我等老去一族喜發思古舊夢,好從那記憶的長河中,盡力用勺子舀些水份,以滋潤趨於枯旱的心田。
家裡的舊物自然成了引發幽情的載體。我不只一次對外子提了這問題:“你猜我們家有多少物件,是由結婚到現在仍有保存的?”屈指一算,已邁向卅八年了!記不起很正常,我不抱奢望。幸好他也能答中我心目中的大部分恩物——梳子、茶杯、鋁梯、溫度計、書籍、相片、郵票、檯布……。然後隔了一段時間,我們再重複話題,又會多發現兩三個目標,就像抖音視頻裡的泥坑釣魚那樣,一條又一條湧出頭來,收穫不盡。在一次家居大掃除中,我瞥見了丈夫的儲物箱內有個別致的小盒子,於是好奇地問他那是啥。他神情詭秘地給我打開一看,竟然是那年蜜月旅行從外地買回來的木製小女孩鈴鐺吊飾。此物在舊居掛了很長時間,且褪了色,搬家前我曾把它扔掉了,想不到他又拾回來並加以珍存。此一息間,在盒子裡面墊着的碎紙條中,我彷彿看到了小物上縈迴的深情,頓時有一絲莫名的觸動。
時光消逝的見證者,又豈止那些默然躺了卅多年的物件?在如歌歲月裡,和自己親近又雋永的物事,一旦成為了平淡的生活習慣,便往往感覺麻木不關情,直到有哪一天驀然想起,才嘆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感。最近才覺察到,卅多年滄海桑田,惟每天承載着我和家人足跡的街道,一直被忽略遺忘,其存在意義沒有怎麼留在個人記憶中,自覺有點抱愧。
我要說的是“士多鳥拜斯大馬路”(Avenida de Sidónio Pais),舊譯“士多紐拜斯”,是本澳自東北至西南的交通要道,為昔日二龍喉馬路重新規劃後的主要路段。那年代澳門街坊多不諳葡文,也不曉得它原是取名於一個葡萄牙總統的名字。於是那個彆扭的譯名便曾一度成為市井笑柄,說那條是什麼“屎忽扭快啲”馬路。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我每天騎自行車往返上學必經士多紐拜斯,這一帶屬於郊外,只有零星簡陋平房、別墅群及歐式大宅。著名地標有二龍喉公園(十九世紀末澳督官邸)、得勝花園(昔日得勝前地)和塔石廣場。當新花園夜總會及愛都酒店相繼落成後,交通漸趨繁忙,不過自行車仍是一般市民和學子常用的代步工具。至七、八十年代隨着本澳人口上升,舊宅相繼拆建,湧現為數眾多的五層大廈群。之後,一幢又一幢的高層樓宇拔地而起,澳門人住房方式起了深刻變化,坐電梯到家的時代來臨。其中一幢一九八四年落成的高樓,爾後便成了我每晚必歸的“膳巢”。
過去澳門人所重視的家庭傳統,體現於核心家庭的種種凝聚文化,例如大時大節相聚進餐,紅白場合出席致意,家族成員互助合作,承傳敬老之道等等。某電視台肥皂劇愛用的經典對白“一家人齊齊整整返屋企吃飯”,就正道出了這種傳統概念最生活化的一面。只是,這凝聚方式逐漸因城市發展和外來文化而演變,離巢燕漸多,喜愛特立獨行;人口老齡化亦間接加深了長幼之間的鴻溝;更不用說這數碼年代,日常往來什麼都依靠線上留言,見面機會減少,親族疏離自然是意料中事。
世道人心轉淡,難得我家成員卻對家庭仍保有那一點點歸心。白天各有各忙的老老少少,每星期總有三、四晚圍桌相聚。如果家飯是磁場核心,那麼食物就是強力磁鐵,把分佈不同地方的“金屬離子”吸附進來。多虧服務我家卅年的保母姐姐,那雙巧手製作的餸菜,在被拍下發送家族群組後,時常得到家人的熱烈回應,然後,腳步自然向着巢裡踏來……。
作為家庭一員,婚後卅多年來,除卻特殊原因,我每晩都回大巢用膳。這春秋不變的習慣,見證着士多鳥拜斯馬路的物換星移。昔日我倆拖着兒子小手走路,如今兒子長大獨行,兩老聯袂而行。已記不清踏破了多少鞋底;穿過了多少趟紅綠燈;沒帶傘的日子被淋了多少場雨;在餅店/超市採購了多少物資;中了多少次樹果子或冷氣機滴水的“頭獎”;沿途遇見了多少個由陌生到熟悉的路人甲,以及每夜在巴士站拿着大包小袋等車歸家的外傭……太多的統計不必去記了。如今我只需知道,踏着陰晴圓缺的月色從小家通往大家,又從大家返回小家的這條馬路,短短十分鐘,每個腳步都印記着和這個家、這個區域連結的永恆記憶。悠悠歲月的每一頓同檯飯,記載了大家庭裡種種無形的依念,儘管各自修行的方式很不一樣。
“大鍋飯”的魅力有多大?看每個人對這飯的觸感如何。於我,飯香是其次,人情才矜貴。感恩士多鳥拜斯馬路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以及種種風物伴我同行,不敢奢求來日風情依舊,只盼有關這條連繫吾家的“紐帶”的所有記憶能鐫刻我心,永不消逝!
雅 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