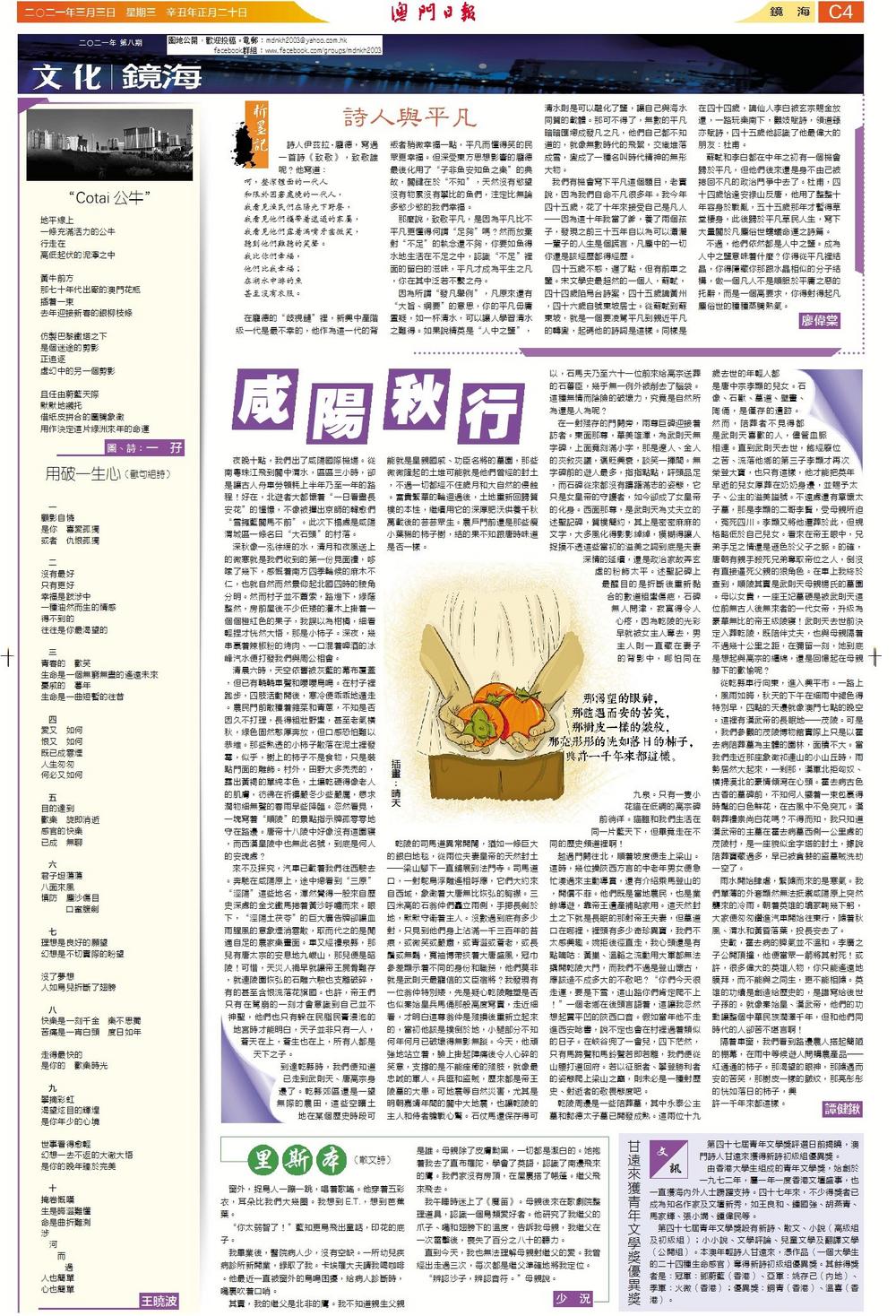咸陽秋行
夜晚十點,我們出了咸陽國際機場。從南粵珠江飛到關中渭水,區區三小時,卻是讓古人舟車勞頓耗上半年乃至一年的路程!好在,北遊者大都懷着“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憧憬,不像被攆出京師的韓愈們“雪擁藍關馬不前”。此次下榻處是咸陽渭城區一條名曰“大石頭”的村落。
深秋像一泓徐緩的水,清月和夜風送上的微寒就是我們收到的第一份見面禮,哆嗦了幾下,感慨着南方四季輪候的麻木不仁,也就自然而然景仰起北國四時的稜角分明。然而村子並不蕭索,路燈下,綠蔭整然,房前屋後不少低矮的灌木上掛着一個個橙紅色的果子,我誤以為柑橘,細看輕捏才恍然大悟,那是小柿子。深夜,幾串裹着辣椒粉的烤肉、一口混着啤酒的冰峰汽水便打發我們與周公相會。
清晨六時,天空依舊被灰藍的幕布覆蓋,但已有轔轔車聲和嚶嚶鳥鳴。在村子裡跑步,四肢活動開後,寒冷便乖乖地遁走。農民門前散種着雜菜和青蔥,不知是否因久不打理,長得粗壯野蠻,甚至老氣橫秋,綠色固然憨厚奔放,但口感恐怕難以恭維。那些熟透的小柿子散落在泥土裡發霉,似乎,樹上的柿子不是食物,只是裝點門面的雕飾。村外,田野大多禿禿的,露出黃褐的單純本色,土壤乾硬得像老人的肌膚,彷彿在祈禱嚴冬少些嚴厲,懇求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早些降臨。忽然看見,一塊寫着“順陵”的景點指示牌孤零零地守在路邊。唐帝十八陵中好像沒有這園寢,而西漢皇陵中也無此名號,到底是何人的安魂處?
來不及探究,汽車已載着我們往西駛去。奔馳在咸陽原上,途中總看到“三原”“涇陽”這些地名,渾然覺得一股來自歷史深處的金戈鐵馬捲着黃沙呼嘯而來。眼下,“涇陽土茯苓”的巨大廣告牌卻讓血雨腥風的意象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閒適自足的農家樂畫面。車又經禮泉縣,那兒有唐太宗的安息地九嵕山,那兒便是昭陵!可惜,天災人禍早就讓帝王屍骨難存,就連陵園恢弘的石雕六駿也支離破碎,有的甚至含恨流落花旗國。也許,帝王們只有在駕崩的一刻才會意識到自己並不神聖,他們也只有躲在民脂民膏浸泡的地宮時才能明白,天子並非只有一人,蒼天在上,蒼生也在上,所有人都是天下之子。
到達乾縣時,我們便知道已走到武則天、唐高宗身邊了。乾縣郊區還是一望無際的農田,這些空曠土地在某個歷史時段可能就是皇親國戚、功臣名將的墓園,那些微微隆起的土堆可能就是他們曾經的封土,不過一切都經不住歲月和大自然的侵蝕。富貴繁華的輪迴過後,土地重新回歸質樸的本性,繼續用它的深厚肥沃供養千秋萬載後的芸芸眾生。農戶門前還是那些瘦小葉稀的柿子樹,結的果不知跟唐時味道是否一樣。
乾陵的司馬道異常開闊,猶如一條巨大的銀白地毯,從兩位夫妻皇帝的天然封土——梁山腳下一直鋪展到法門寺。司馬道口,一對鴕鳥浮雕遙相呼應,它們大約來自西域,象徵着大唐無比恢弘的胸襟。三四米高的石翁仲們矗立兩側,手摁長劍於地,默默守衛着主人。沒數過到底有多少對,只見到他們身上沾滿一千三百年的苔痕,或微笑或嚴肅,或青澀或蒼老,或長鬚或無鬍,寬袖博帶挾着大唐盛風,冠巾參差顯示着不同的身份和職務,他們莫非就是武則天最寵信的文臣宿將?我發現有一位翁仲特別矮,先是疑心乾陵雕塑是否也似秦始皇兵馬俑那般高度寫實,走近細看,才明白這尊翁仲是殘損後重新立起來的,當初他該是撲倒於地,小腿部分不知何年何月已破壞得無影無蹤。今天,他頑強地站立着,臉上掛起陣痛後令人心碎的笑意,支撐的是不能痊癒的殘肢,就像最忠誠的軍人。兵匪和盜賊,歷來都是帝王陵墓的大患。可地震等自然災害,尤其是明朝嘉靖年間的關中大地震,也讓乾陵的主人和侍者膽戰心驚。石仗馬還保存得可以,石馬夫乃至六十一位前來給高宗送葬的石蕃臣,幾乎無一例外被削去了腦袋。這種無情而陰險的破壞力,究竟是自然所為還是人為呢?
在一對殘存的門闕旁,兩尊巨碑迎接着訪者。東面那尊,華美雄渾,為武則天無字碑,上面竟刻滿小字,那是遼人、金人的夾敘夾議,褒貶興衰,談笑一揮間。無字碑前的遊人最多,指指點點,評頭品足,而石碑從來都沒有躊躇滿志的姿態,它只是女皇帝的守護者,如今卻成了女皇帝的化身。西面那尊,是武則天為丈夫立的述聖記碑,質樸簡約,其上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大多風化得影影綽綽,模糊得讓人捉摸不透這些當初的溢美之詞到底是夫妻深情的延續,還是政治家故弄玄虛的粉飾太平。述聖記碑上最醒目的是折斷後重新黏合的數道粗蠻傷疤,石碑無人問津,寂寞得令人心疼,因為乾陵的光彩早就被女主人奪去,男主人則一直藏在妻子的背影中,哪怕同在九泉。只有一隻小花貓在低調的高宗碑前徜徉。貓雖和我們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但畢竟走在不同的歷史頻道裡啊!
越過門闕往北,順着坡度便走上梁山。這時,幾位操陝西方言的中老年男女便急忙湊過來主動導賞,還有介紹乘馬登山的,開價不菲。他們既是當地農民,也是業餘導遊,靠帝王遺產補貼家用。這天然封土之下就是長眠的那對帝王夫妻,但墓道口在哪裡,裡頭有多少奇珍異寶,我們不太感興趣。婉拒後徑直走,我心頭還是有點嘀咕:黃巢、溫韜之流動用大軍都無法撬開乾陵大門,而我們不過是登山懷古,應該造不成多大的不敬吧?“你們今天很走運,要是下雪,這山路你們肯定爬不上!”一個老鄉在後頭言語着,這讓我忽然想起賈平凹的陝西口音。假如當年他不走進西安唸書,說不定也會在村裡過着類似的日子。在峽谷兜了一會兒,四下茫然,只有馬蹄聲和馬鈴聲若即若離,我們便從山腰打道回府。若以征服者、攀登勝利者的姿態爬上梁山之巔,則未必是一種對歷史、對逝者的敬畏態度吧。
乾陵周邊是一些陪葬墓,其中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已開發成熟。這兩位十九歲去世的年輕人都是唐中宗李顯的兒女。石像、石獸、墓道、壁畫、陶俑,是僅存的遺跡。然而,陪葬者不見得都是武則天喜歡的人,儘管血脈相連。直到武則天去世,飽經廢位之苦、流落他鄉的第三子李顯才再次榮登大寶,也只有這樣,他才能把英年早逝的兒女厚葬在奶奶身邊,並賜予太子、公主的溢美謚號。不遠處還有章懷太子墓,那是李顯的二哥李賢,受母親所迫,冤死四川。李顯又將他遷葬於此,但規格略低於自己兒女。看來在帝王眼中,兄弟手足之情還是遜色於父子之脈。的確,唐朝有親手殺死兄弟奪取帝位之人,倒沒有直接逼死父親的狠角色。在車上我終於查到,順陵其實是武則天母親楊氏的墓園。母以女貴,一座王妃墓硬是被武則天這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女帝,升級為豪華無比的帝王級陵寢!武則天去世前決定入葬乾陵,既陪伴丈夫,也與母親隔着不過幾十公里之距,在彌留一刻,她到底是想起與高宗的纏綿,還是回憶起在母親膝下的歡愉呢?
從乾縣車行向東,進入興平市。一路上,風雨如晦,秋天的下午在細雨中褪色得特別早,四點的天邊就像澳門七點的晚空。這裡有漢武帝的長眠地——茂陵。可是,我們參觀的茂陵博物館實際上只是以霍去病陪葬墓為主體的園林,面積不大。當我們走近那座象徴祁連山的小山丘時,雨勢居然大起來,一剎那,漢軍北拒匈奴、橫掃漠北的豪情傾瀉在心頭。霍去病古色古香的墓碑前,不知何人擺着一束包裹得時髦的白色鮮花,在古風中不免突兀。漢朝葬禮崇尚白花嗎?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漢武帝的主墓在霍去病墓西側一公里處的茂陵村,是一座貌似金字塔的封土,據說陪葬寶藏過多,早已被貪婪的盜墓賊洗劫一空了。
雨水開始肆虐,緊隨而來的是寒氣。我們單薄的外套顯然無法抵禦咸陽原上突然襲來的冷雨。朝着英雄的墳冢鞠幾下躬,大家便匆匆鑽進汽車開始往東行,隨着秋風、渭水和黃昏落葉,投長安去了。
史載,霍去病的脾氣並不溫和。李廣之子公開頂撞,他便當眾一箭將其射死!或許,很多偉大的英雄人物,你只能遙遠地膜拜,而不能與之同生,更不能相隨。英雄的功績是創造給歷史的,是譜寫給後世子孫的。就像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功勳讓整個中華民族潤澤千年,但和他們同時代的人卻苦不堪言啊!
隔着車窗,我們看到路邊農人搭起簡陋的棚幕,在雨中等候遊人問購農產品——紅通通的柿子。那渴望的眼神,那隨遇而安的苦笑,那樹皮一樣的皺紋,那亮彤彤的恍如落日的柿子,興許一千年來都這樣。
譚健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