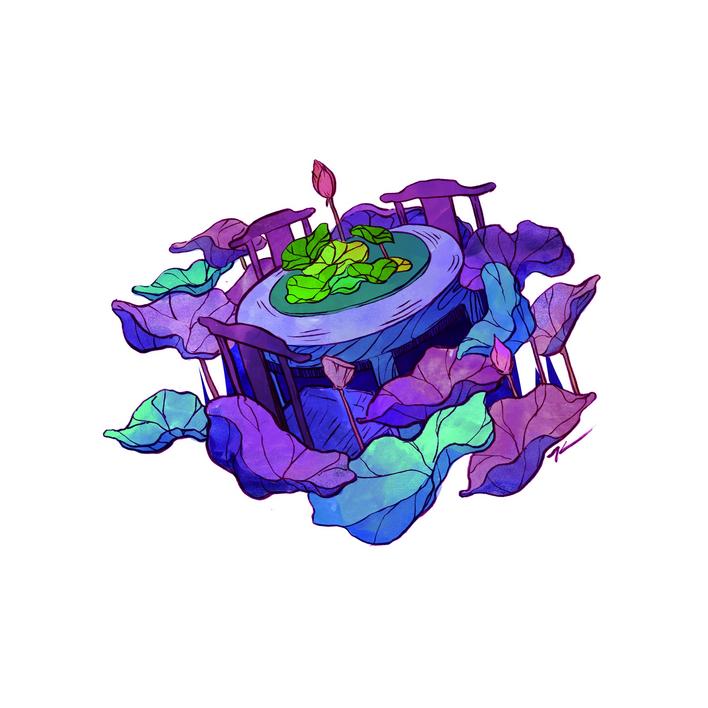
這荷花怎麼還不開?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以天真著稱的翠縷問:“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淡定回應:“時候沒到。”
荷花未開,詩人不急,嫩莖、花苞、初荷,皆可入詩;待荷花綻一兩分,老饕們卻早已等得心焦。
初夏時候,若人在北京,就愛往什刹海看荷花;若身處澳門,就該到盧廉若公園。荷花不吃人間煙火之姿,固然靈氣逼人,但更令我遐想聯翩的,是一池生命力旺盛的荷葉。雜亂交錯,互相比賽誰長得快長得高大。面對如詩的畫面,儒士會吟誦“出污泥而不染”,道家早與荷葉底下的魚兒物我相忘,我此等凡夫俗子看到的,都是荷葉蒸雞、蓮藕炆豬肉、蓮子百合糖水、籠仔荷葉飯。
荷花是夏日最美的風物,中看中用,渾身是寶——荷花養顏、荷葉清香、蓮梗爽嫩、蓮藕粉糯、蓮子清心、蓮蓬解熱,就連《紅樓夢》裡薛寶釵的冷香丸配方,也要用上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蓮藕和蓮子製法多端,在此不贅,只談風動心也動的荷花荷葉。
廣東人特別鍾情荷葉,蒸飯、煮湯皆宜,用來蒸蟹肉、蝦肉、雞肉,清香四溢,把食材提升了一個檔次。在向來有“蓮花寶地”之稱的澳門,以荷入饌更是常事,簡單如冬菇荷葉蒸雞,正是家父的看家本領之一。夏日的粵菜餐館可以缺鮑魚,但不能缺荷葉,高級酒家期間限定的十二道“荷花宴”,把荷花全身都用上,唯獨荷葉的神助攻最具鋒芒。
荷香有助去肉的膩味,所以古代的肉舖常備荷葉。就提升香味而言,荷葉比荷花中用。荷葉不論新鮮還是晾乾,都是廚娘的法寶,難怪《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精明能幹的探春對着一池破殘的荷葉,感懷身世,覺得連“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荷香在古代烹飪中的重要性,和今人動不動加幾滴松露油的動機相同,境界卻高遠多了。
廣東人夏天常常用乾荷葉、冬瓜、薏仁煲湯,清熱消暑。古人則愛用荷葉煮粥,如清代黃雲鵠《粥譜》中有“荷鼻粥”,荷鼻即葉蒂,可連莖葉同用,“以之煮粥,香清佳絕”,更被清代的養生專家曹庭棟列為上品。當代荷葉粥的做法,多以鮮荷葉作鍋蓋,以水汽萃取香氣,一滴入魂;或把荷葉剪碎與粳米同煮,簡單養生。
荷葉還可以做羹湯。比如《紅樓夢》三十五回,寶玉被老爸打得皮開肉綻、躺在榻上動彈不得之際,最想吃的療癒食物,居然是“口味不算高貴”的蓮葉羹。煮那碗“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既要張羅模具,又要“新荷葉的清香”,還要殺雞,做起來費勁兒。大費周章弄來蓮葉羹後,寶玉喝兩口就故意說沒滋沒味兒,反用來逗玉釧兒吃他的口水。搞半天,那碗奢靡的蓮葉羹不是拿來去瘀療傷,不是用以滿足口腹之慾,而是公子哥兒用來折騰人、尋開心的。被揍一次,原來就能得一次隨便點菜的權利,我三不五時捱打的童年算是白過了。
更矯情的荷葉用法,是直接把荷葉當作酒杯,古人稱之為“碧筒飲”,荷葉杯因而有“碧筒杯”的別名。碧筒飲此等風流雅事,最早始於魏晉。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中“酒食”篇記載:“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筒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好一個“香冷勝於水”!比當代的甘蔗渣、竹製環保吸管講究,比花巧的昂貴醒酒器又有效多了。
到了唐代,士大夫們飲碧筒酒以消夏的興致有增無減。職場上不得志而寄情詩酒的白居易,雖有“寂寥荷葉杯”等句,但唐人以荷葉飲酒的畫面,總體還是熱鬧不羈的。趙璘《因話錄》中記載唐代宰相李宗閔和賓僚於盛夏之夜,如何在水邊浮誇地飲宴作樂:“暑月臨水,以荷為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箸刺之,不盡則重飲。”先取來帶莖的荷葉,以筷子刺穿荷心,使刺孔與空心的荷莖相通,然後在荷葉中灌進美酒,再將荷莖彎成象鼻狀,從莖的末端吸酒。如此現取現用,頗有順手拈來的野趣,也像大學新生用漏斗喝啤酒的豪飲派對。
唐代的建築風格,在日本京都得到一定保存,就連唐人飲碧筒酒的習俗也遺留下來,宇治的三室戶寺至今還保留着仲夏喝“蓮酒”(ハス酒)的活動,每年吸引大批遊客來慕古嘗鮮。加強版的碧筒酒,直接用上搗碎的蓮花,如後唐馮贄《雲仙雜記》引《叩頭錄》所記的“擣蓮花製碧芳酒”,清熱涼血的效果也加倍。經過荷莖浸潤的美酒,平添一份清苦綿長的滋味,單是看酒水點點成珠,在碧葉上晃來晃去,已夠銷魂了吧。
以為詩詞中只有梅蘭竹菊就大錯特錯了,亭亭的荷花、田田的荷葉,可是古人主要的抒情對象,相關詩作的花樣也多。荷葉杯在唐詩宋詞中出場率之高,如戴叔倫的“茶烹松火紅,酒吸荷葉綠”,曹鄴的“乘興挈一壺,折荷以為盞”,蘇東坡的“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等都有提到。若論臨場感,當數歐陽修的《漁家傲》:“花底忽聞敲兩槳。逡巡女伴來尋訪。酒盞旋將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裡生紅浪。花氣酒香清廝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閣在沙灘上。”花氣、酒香,加上女伴、倒睡、醉駕,假若要來一場宋代名士風流象徵物的票選,正襟危坐“點茶”用的兔毫盞,又怎敵那渾然天成的豪放荷葉杯呢?
既有荷葉杯,別出心裁、腦洞大開的古人,又怎會想不到以荷花為杯?元人陶宗儀在《輟耕錄》便有荷花杯的介紹:“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將小巧的金酒杯塞進荷花,又衛生又高級,飲時兩手並用,像小蜜蜂那樣往花裡埋首啜飲,與古人的寬袍大袖正匹配。陶宗儀覺得荷花杯的風致遠在荷葉杯之上,美其名曰“解語杯”。喝完酒後,解語杯還另有妙用,擷取荷瓣,夾於畫冊,可以避免蟲蛀。但荷瓣易發霉,畫留霉跡,亦為憾事。
美酒當然要配小吃。佐酒之物,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暑月,命客泛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鮓他葉內。俟舟廻,風薰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鮓。真佳適也。”湖中泛舟,賞荷是幌子,重點是取荷葉盛酒,佐以用荷葉包裹的醃魚,既省卻多餘的杯碟器皿,酒與小吃又多添荷葉的清香,此舉可是把大自然當作自家廚房和即興小酒吧。《山家清供》中還有一道“蓮房魚包”,製法繁複,但估計也是上佳的下酒菜:“蓮花中嫩房,截去底,剜穰,留其孔。以酒漿、香料和魚塊實其內,仍以底座,甑內蒸熟,或中外塗以蜜。”元代鄒鉉《壽親養老新書》中介紹的“蓮房脯”,蓮房已非器具,而是食材:“取嫩蓮房,去蒂,又去皮,留中間,絡入灰煮浥。一如芭蕉法。焙乾,以石壓,令匾,作片收之。”更像是蓮香脆片,也是可鹹可甜的下酒佳物。
近年手搖飲品店裡的所謂復古“荷花茶”,亦足見雲泥之別。“荷花熏茶”最早見於據傳為元代大畫家倪雲林的私房菜譜《雲林堂飲食制度集》,另見於明人顧元慶的《茶譜》、屠隆的《考槃餘事》。“雲林堂”熏製蓮花茶的程序相當考究:“蓮花茶,就池沼中,蚤飯前、初日出時,擇取蓮花蕊略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繩縛扎定。經一宿,明蚤連花摘之,取茶紙包,曬乾。如此三次,錫罐盛,口收藏。”要在天剛破曉之時,在荷塘選取一朵微綻的蓮花苞,往苞中灌滿茶葉,然後讓花瓣重新合攏,用麻繩將花苞綑紮,確保其閉合不散。至次日早晨,把整朵蓮花摘下,用紙包着茶葉,拿去曬乾。接下來的清晨,需再選擇一株微綻的蓮花,將已熏過一次的茶葉二度埋於苞內,如此反覆三次,方算大功告成,往後只要用密封性好的錫罐儲藏,則秋冬春三季,隨時也可品味到夏日的清香氣息。
較真起來,荷花茶的製作過程,比賈府的蓮葉羹更磨人更爆肝,不是飯來張口、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書生能體會的。清代文人沈復在《浮生六記》裡記載了妻子芸娘窨製荷花茶的過程,放在當代語境,不就是撒狗糧式的另類放閃。“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條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利用荷花黃昏開始含苞、於隔日清晨盛開的特點,在晚上,用一個小紗袋盛些茶葉,輕輕將蓮苞的花瓣撥開,把茶葉袋放到花心上,然後讓花苞自動閉合。到了第二天早晨,蓮花開始綻放,在花胎裡窨了一夜的茶葉袋也飽沁蓮芬,以之泡茶,香韻獨特。清晨早起,只為給清貧的丈夫一點高級的雅趣,芸娘的荷花茶不是食材,是滿滿的愛——含蓄直接、不求回報的愛。芸娘的荷花茶製法,只窨一次,又少了紙包烘乾的步驟,剛窨完的荷花茶水分多,香氣淡薄又不耐放,但現做現喝,更見心意。
荷花茶的極致,是用荷露來煎。乾隆帝有一首〈荷露煮茗〉詩云:“平湖幾里風香荷,荷花葉上露珠多。瓶罍收取供煮茗,山莊韻事真無過。”作為“品水專業戶”的乾隆對飲用水十分講究,認為“水以輕為貴”,龜毛得整天帶着特製銀斗去量稱各地水源,最後選定重一兩的玉泉水為御用水,但“輕於玉泉者唯雪水及荷露”,可見荷露的口感有多高級。比玉泉水還要輕的雪水並不常有,又非地下所出,古人認為多喝有頭風,不是“入品”之水。荷露比雪水更難儲存,一國之君的乾隆帝也只能一路饞到夏秋之際,頻頻命人取荷露來烹茶。
荷花除了配酒製茶,還可以製醋。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就詳細地記載了做“蓮花醋”的作法:“白麵一斤,蓮花三朵搗細,水和成團,用紙包裹,掛於當風處,一月後取出。以糙米一斗,水浸一宿,蒸熟,用水一斗釀之,用紙七層密封定。每層寫七日字,過七日揭去一層。至四十九日,然後開封篘出,煎數沸,收之。如二糟有味,用滾水再釀,儘有日用。忌生水、濕器收貯。”蓮花醋還沒有機會嘗到,但用來配夏日的清爽沙拉,估計比甚麼櫻花醋、洛神花醋、玫瑰花醋、薰衣草醋、牡丹花醋都要對味,能和荷花在餐桌上一較高下的,在我心中唯有與甜品絕配的桂花。
愛荷花的,不一定能像周敦頤那樣清清白白地名留青史。漢昭帝迷荷花、嚼荷花、穿戴荷花,還用荷葉遮陽,卻被寫進《太平廣記》裡“奢侈”那一章。漢昭帝即位不久便建了一個廣大的“淋池”,裡頭種滿了一莖四葉的“分枝荷”,這種荷花就算凋謝了,“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連宮女們也趨之若鶩,把荷花片當口香糖用。這算是暴殄天物麼?只能說是物盡其用了吧,漢昭帝的罪狀在於賞荷賞過頭了。
被喻為極簡性冷淡風鼻祖的宋人,飲食上也知道少即是多,荷花主要用來製作糕點,如《清異錄》記載:“郭進家能做蓮花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據《清稗類鈔》等文獻記載,南京的雞鳴寺、蘇州的寒山寺等江南寺院,其時供應的素食也有用荷花入饌。對老饕而言,荷花早就不是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了。相傳慈禧太后愛把炸荷花片當零嘴,每到荷花盛開的季節,命宮女們採摘飽滿、完好的荷花送去御膳房,御廚將肥美的花瓣浸在用雞蛋、雞湯調好的麵糊中,炸至金黃酥脆。老佛爺就愛它的清爽不膩,齒頰留香,算是山珍海錯之間的清口菜。
古代人吃荷葉荷花的千奇百趣,如今只能隔着古書口水直流,幸而有些美食是歷久不衰的,如山東濟南名菜之一的“炸荷花”。對比上述林林種種的荷花料理,當代炸荷花的製法實而不華,在兩片荷花瓣中抹上細滑的紅豆蓉,蘸麵糊,熱油炸,吃起來別具風味。真正的難處在於沒有農藥的荷花不易得,公園裡廣場裡的荷花又不能亂摘,名副其實只能遠觀了,不是教“蓮花寶地”裡的吃貨們活受罪嗎?
“炸荷花”有多好吃,老舍還為此專門寫了短文〈吃蓮花的〉。老舍搬到濟南後種了兩盆白蓮,泥是由黃河拉來的,水用趵突泉的,好不容易養到開花了,本想用來欣賞作詩,高雅一番,來訪的本地朋友卻二話不說摘了來交給廚子,吩咐“把這用好香油炸炸。外邊的老瓣不要,炸裡邊那嫩的”。廚子是老舍由北平請來的,和老舍一樣不懂濟南的典故,還以為香油炸蓮瓣是甚麼偏方呢。
“這治甚麼病,燙傷?”廚子問。
友人笑了:“治燙傷?吃!美極了!”
老舍本來寫了一大堆詠荷的詩文,單是“亭亭玉立”這四個字就被他用了七十五次。待老舍吃完那妙不可言的炸荷花片,知道詩已不管用,把詩稿全燒了。
袁紹珊